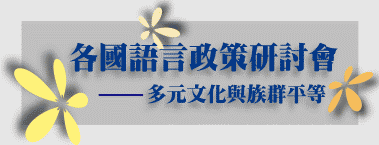
|
|
|
越南「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 蔣為文◎德州大學語言所 |
|
|
一 前言 越南曾受中國的直接統治達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稍後雖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而獨立建國,卻仍與中國維持一定的藩屬關係,直到1945年胡志明宣佈越南獨立後才正式劃清與中國的關係。 在中國統治的期間,漢字被採用為正式的官方文字。稍後的藩屬國期間民間發展出民族文字「 雖然台灣也在十七世紀初經由荷蘭傳教士傳入羅馬字,【1】使得羅馬字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書寫文字,然而隨漢移民遷入台灣的漢字卻後來居上,成為當今台灣社會的書寫文字之主流。 本論文以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例來探討語言使用、階級、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何以越南能成功地從漢字轉變為羅馬字。越南之所以能恢復使用越南語、拋棄漢字並採用羅馬字,並非只是胡志明個人獨裁、強制推行越語政策此一因素,而是有其主、客觀的條件才能達成。本文指出越南羅馬字化成功有內在和外在二大因素:內在因素包含“具讀寫能力”和“反封建社會”的需求;外在因素包括“去中國化”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潮流。 二 漢字文化圈之歷史背景 所謂的「漢字文化圈」,【2】是指曾經或還在使用漢字的國家,諸如越南、韓國、日本、台灣和中國等。在這區域內,中國曾扮演主宰的角色,在政治、文化上對其他國家具支配的影響。 公元前111年,中國將越南納入直接統治,直到十世紀越南才脫離中國而獨立。公元前108年中國征服古朝鮮,設立「樂浪」、「真番」、「臨屯」和「玄菟」四郡;直到四世紀,「高句麗」人攻佔「樂浪」郡,朝鮮才脫離中國的統治。日本從先秦時代即有和中國接觸的紀錄,漢武帝更曾賜日本「漢委奴國王」金印;雖然日本未受中國直接統治,但是在漢朝和唐朝盛世的影響力下中國也變成日本學習模仿的對象。 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除了政治上受中國支配外,另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漢字」、引進「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他們在借用漢字後,均發覺漢字無法完整表達他們的語言;於是利用漢字做「訓讀」、「音讀」或造新漢字來應付這個問題,甚至後來更慢慢發展出新的文字系統,譬如越南的「
就語言文字學習效率的角度來說,漢字不但複雜、難學,【3】而且那些用「文言文」書寫的古典經書更是難懂;於是造成古典經書的「解釋權」掌握在精通漢字的文人手裡。相形之下,打赤腳的工農階級平常忙於耕作、勞動的時間都不夠了,那有時間“十年寒窗”苦讀漢字和經典。於是漢字文化圈在長期使用漢字的情況下,逐漸形成“掌握漢字的文人統治階級”和“不懂漢字的被統治階級”的對立。這種階級對立的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逐漸興起後才開始有轉變。 那些廣大的勞動階級為著紀錄自己的日常生活語言,而發展出「 三 越南之外來統治與民族獨立運動 在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中原之後,他又繼續出兵征伐「嶺南」,【4】並於公元前214年兼併嶺南地區。秦帝國於公元前207年崩潰後,前秦將領「趙陀」趁機佔領嶺南並於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國」並定都於「番禺」【5】(張榮芳、黃淼章1995:56-68)。公元前111年中國漢朝的漢武帝出兵殲滅「南越國」,並在其地設「交趾部」,分為九郡。其中三郡「交趾」、「九真」和「日南」相當於現今「越南」之北部和中北部地區。從那時起越南第一次正式被納入中國的版圖;而在越南也將此歷史稱為第一次北屬時期(陳重金1992:28)。【6】 公元939年,越南利用唐朝末年大亂之時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而獨立;雖然是獨立,但是越南仍必須定期向中國朝貢並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這藩屬關係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段法國侵略越南,才由法國取代中國的宗主國地位。(SarDesai 1992:19) 在越南獨立、但稱臣於中國的期間,越南也和中國一樣建立起封建的社會制度。特別在李朝(公元1010-1225)和陳朝(1225-1428)時期,越南從中國引進各式政治、文物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和「儒家思想」來穩定朝代的封建基礎。換一句話說,雖然越南不再受中國的直接統治,但是中國對越南仍有極大的影響。(SarDesai 1992:21)這也是為什麼越南已故近代的歷史學者陳重金(Tran Trong Kim 1882-1953年)在他的名著《越南通史》 裡感嘆地說:
公元1858年,法國利用傳教士受迫害做藉口而向越南出兵。越南末代朝廷「阮朝」不敵法軍,而於1862年割讓南部「嘉定」、「邊和」、和「定祥」三省給法國以求和。當然法國並不以此為滿足,稍後並陸續侵佔其他各省,終於於1885年完全征服越南。越南遭受法國襲擊之時亦曾向中國求援,然當時之中國已病入膏肓,所派遣前來應戰之軍隊並無法有力遏止法軍之侵略。最後中法雙方於1885年簽定協議停戰的「天津條約」。在條約中,中國正式放棄對越南之宗主國地位並承認越南改由法國保護(陳重金1992:406)。從此越南受法國的直接統治,直到1945年胡志明利用二次大戰剛結束之國際局勢宣布越南獨立並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之後,情勢才開始改變。 在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之後,法國及各國政府並未馬上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之合法性,法國甚至起兵鎮壓獨立運動者。為求建國,越南人民也興起10年的抗法獨立戰爭,直到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Geneva Accords)才確立越南獨立的合法性;然而在歐、美、蘇聯及中國的介入下,越南隨即被一分為二,也就是我們所認知的「南越」和「北越」。南北分裂之局面持續到1975年,當美軍從越南撤退且南越首都「西貢」淪陷於越共手裡,才由越南共產黨一統南北。南北越於1976年正式合併,改國號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定都於「河內」;此統一局面一直維持到現今仍不變。 四 越南之文字傳統與變革 越南為一多族群、多語言的國家。越南在1998年的人口總數為七千七百萬。(Grimes 2000)根據越南官方正式統計與認可,越南共有54個民族,其中的「京族」約佔87%的越南人口。(附錄一)京族所使用的語言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越南語。越南境內的語言種類與數量則因學者之分類而異;根據Ethnologue的統計,越南現有93種語言。(Grimes 2000) 越南的傳統書寫系統是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文為正統地位。之後民間雖有「 漢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約開始於趙佗的「南越國」時期(Nguyen 1999:2)。在中國直接統治的時期也一直延用漢字為書寫系統。即使在十世紀越南獨立後,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廣「儒學」【8】(Nho hoc)與建立「科舉制度」,【9】使得漢字的正統地位在二十世紀前牢不可破。漢字在越南也叫做「字儒」(Chu Nho),【10】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字。一般來說,漢字用於行政、教育(科舉)、學術著述、和古典文學之創作。(Nguyen 1999:3-4) 越南在借用漢字後,發覺漢字無法完整表達越南的日常用語,於是民間慢慢發展出具越南特色的
雖然 第一,受中國價值觀之影響。因為漢字在中國被視為唯一的正統文字,而越南又把中國奉為宗主國,致使越南各朝代均把漢字奉為圭臬、不敢對之不敬。唯一少數欲推行 第二,受科舉制度之束縛。由於各朝代均將漢字列為正統、並列在科舉考試之內,致使想當官的文人不得不學漢字、背誦四書五經等。一但這些人考試入取、功成名就後,當然就繼續擁護漢字的正統地位,因為這樣才能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那些沒入取、略懂漢字的文人因生活週遭與勞苦大眾接觸,為了反應實際需要,就傾向於使用 第三, 五 越南羅馬字之興起 越南的書寫文字一直到十七世紀,紀錄「音素」(phoneme)的羅馬字的出現才有重大的轉折。雖然羅馬字在那時已出現,卻要等到二十世紀才有力量完全取代漢字的地位。羅馬字在越南的發展可以分做四個階段:第一,十七世紀初到19世紀中期的教會使用期;第二,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法國殖民者推廣使用期;第三,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越南民族主義者推動使用期;和第四,1945年以後的正統地位時期。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時候,歐洲傳教士逐漸到越南來傳教。傳教士們為了容易學好越語並與當地越南人溝通,於是利用歐洲人熟悉的羅馬字來替越南語設計一套新的書寫系統。【15】和多數的文字發展歷史一樣,【16】越南羅馬字的發展並不是由一人於一天之內發明出來的,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由一群人共同累積經驗而“約定俗成”起來的。【17】在經歷各傳教士的努力下,第一本越南羅馬字的詞典「越南、葡萄牙、拉丁語三語對照詞典」【18】於1651年由法籍傳教士「得路」【19】出版。(Do 1972)「得路」和其「越葡拉」辭典對越南羅馬字的貢獻就如同「麥都思」【20】和他於1837年所出版之「福建方言字典」【21】對台灣教會「白話字」【22】的奠基性貢獻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扮演集大成、並將付諸出版的第一人。「得路」的羅馬字拼字系統在歷經不同時期的稍微修改後,成為當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國語字」。 在十九世紀後半段之前,越南羅馬字主要只在教會之中流傳。隨著法國殖民者的到來,羅馬字才逐漸提升地位與普遍被使用。(Vien Van Hoc 1961:21-22)譬如,法國殖民者將羅馬字列入學校課程,【23】而且於1865年在越南南部由當時的官方發行第一份羅馬字報紙「Gia Dinh Bao」(嘉定報);越南羅馬字也從這時起叫做「Chu Quoc Ngu」(國語字)。(Vien Van Hoc 1961:22)「嘉定報」就如同台灣1885年出版的第一份羅馬字報紙「Tai-oan-hu-sia Kau-hoe-po」【24】一樣,具帶頭普遍羅馬字之貢獻。另一個例子是,南部總督於1882年簽定一份規定所有越南語的公文必須用羅馬字的議定。(Vien Van Hoc 1961:22-23) 法國之所以推動越南羅馬字,主要有以下之原因: 第一,法國殖民者認定漢字是法國人與越南人之間的障礙。由於越南長期奉中國為宗主國、並透過漢字學習中國文化與價值觀,如果讓越南人繼續使用漢字無疑是讓越南保持與中國的親密關係。為讓越南斷絕與中國的關係、並改為親近法國,勢必要用羅馬字取代漢字。【25】 第二,羅馬字是讓越南人從越語過渡到法語的重要媒介。法國殖民者認為當越南人掌握著越南羅馬字後就容易進一步學習法語、最後並完全轉換到使用法語。所以推行羅馬字是推行法語的重要手段之一。(DeFrancis 1977:131-134) 總之,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羅馬字成功取代漢字這一事件上扮演著「催化」的角色。雖然殖民者的初衷是要利用羅馬字來推行法語,卻無形中營造越南羅馬字初期成長的空間。 雖然在法國殖民者的推動下,越南羅馬字在十九世紀後期有比以前較普遍,然而它的推行成效仍然相當有限。(DeFrancis 1977:69)羅馬字的推行要在二十世紀初透過越南本土的民族主義者的鼓吹後才有顯著的進展。(DeFrancis 1977:159)原因是:在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氣氛下,使用外來的羅馬字被視為是趨附外來殖民政權的行為。然而當越南民族主義者感受到羅馬字簡單、好學、是教育民眾的好工具時,他們已把羅馬字本土化成為對抗外來統治的利器。 鼓吹羅馬字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代表性團體首推「東京義塾」的成員。【26】「東京義塾」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二十年代台灣的「文化協會」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文化協會」並不注重羅馬字、只倡導漢字白話文。這差別也注定了羅馬字在台灣和越南有截然不同的發展命運。 「東京義塾」的成員主要是一些留學日本的越南知識份子。他們於1907年在「河內」設立「東京義塾」學校,用來傳授西方思想與科學新知等。他們認為要達成啟發民智的目的,非得透過越南羅馬字不可。所以他們的第一要務就是要普及羅馬字;透過羅馬字來教育民眾、讓大眾有知識,以對抗法國殖民統治。「東京義塾」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一年,旋即被法國殖民者強制關閉,然而他們的主張在知識份子中卻廣為受到認同與支持。之後,「推廣羅馬字」逐漸成為越南民族主義者中的普遍主張與推動要點,並興起一股興學、辦羅馬字報的風潮。(Vuong & Vu 1980:20-32)據估計,至1930年,全越南共有75種羅馬字報紙。(Hannas 1997:86) 雖然羅馬字在民族主義者的推行下有顯著的成就,然而並不代表羅馬字已完全取代漢字和法文。羅馬字的地位在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後才進一步提升為國家唯一正式書寫文字的地位。胡志明於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獨立並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後,於9月8日又隨即公佈政府全面推行羅馬字教育。他於該年十月份又發表一份呼籲全國同胞共同掃除文盲的公開信,在信中他說:
據估計,1945年全國識字人數大約為20%;在全面推行羅馬字後,在1953年已提升到70%。(DeFrancis 1977:240) 綜觀越南從漢字與 外在因素是指越南在長期受中國及法國殖民統治之下,試圖利用越南羅馬字做為文化獨立的基礎、以進一步保障民族政治之獨立。在二次大戰當中,越南面對法國、日本、英國、美國及中國等之既鬥爭又聯合的局勢,【27】不得不思考為民族獨立鋪路之方法。在四十年代,日軍為侵略中國而進軍越南,打算以越南做為攻擊中國西南地區的根據地。對中國來說,遣軍進入越南以掃除日軍根據地是有需要的。然而當時仍控制越南的法國當局卻對中國懷有疑慮,深怕中國軍隊一入越南將使越南重回中國之手裡。對越南的領導人來說,如何利用各國的矛盾讓越南獲得獨立乃是當務之急。胡志明對中國當然相當了解,他也怕中國利用掃蕩日軍做藉口而佔領越南。於是他的策略是力阻中國軍隊進入越南,(蔣永敬1971:107)並策動反中國之運動。(蔣永敬1971:228-240)「羅馬字」在這時也成為確保政治、文化獨立之最好選擇。 內在因素是指反封建、反知識壟斷的廣大需求。就如同胡志明在掃除文盲的公開信中所提及的,如何讓那廣大的未受教育的群眾擁有新知識以求國富民強是當務之急。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越南封建社會中,唯一外來的主要威脅為中國;在那情形之下,採用漢字雖然會造成多數的勞苦階級成為文盲,卻可以消除中國的侵略慾並滿足越南封建朝廷的既得利益。然而,到二十世紀後,越南所要面對的不只是中國,而是接連而來的西歐及日本帝國主義。 六 結論 從越南這個例子可以印證Gelb (1952:196)所說的「只有在傳統文字發源地以外之邊外人才敢於做革命性的文字改革並獲得極大成就」。當台灣人還徬徨在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抉擇當中,我們可以預期台灣人對維護自己的語言並不會太堅持。越南的民族主義領導者因為有強烈的越南民族國家意識,加上反封建、反知識壟斷的潮流鼓動下,因而能破釜沉舟的對漢字進行改革、最後並用羅馬字將之取代。相形之下,台灣人能嗎?台獨運動者有這種覺悟嗎?多數台獨運動者總是認為台灣人的獨立意識不夠強,然而卻很少領導者願重視文化上“去中國化”的重要性;甚至隨那些統派人士起舞,認為推行台語文【29】有礙台灣的族群和諧。事實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的模糊剛好反映在他們對台語文的曖昧態度上;他們對使用台語文的不確定性也顯示在台灣人對台灣前途定位的畏懼。 有人說:語言和獨立建國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然,他們沒有絕對的關係;但是他們有相對的關係。如果台灣人天生就講北京話,台灣人當然還有權利主張台灣獨立;然而台灣人天生是講台灣話的,他們是因為受政治壓迫才講北京話的,恢復講台灣話對台灣認同是有幫助的。Ross (1979:4)指出,語言和認同是否有關聯,必須從不同情境當中來判斷。就台灣的例子來說,長期以來,所謂的“國語”(台北華語)、“國字”(繁體漢字)均被統派用來作為建構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想像的基本要素。在此情形下,語言和認同的強烈關係已先被統派連結住了;欲拆除中華民族的神話,當然也就不得不從語言、文字下手。蔣為文針對台灣大學生所做的調查結果也顯示:第一,個人的族群認同未必需要具備族語的能力;然而,具備族語能力卻可以強化個人的族群認同。(Chiung 2001a)第二,“台語文”和“台灣的國家認同”有正相關、加分的效果。(Chiung 2001b)以上這說明:推行台灣語文對建構台灣人意識是有正面的幫助。 基本上,政治和文化是“共生”的關係。政治可以影響文化,文化也可以決定政治。以越南為例,越南在受中國的政治、文化二千年的影響後,能獨立成功成為一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越南傳統的政治、文化架構在十九世紀法國勢力進入後才逐漸動搖。法國以武力建立殖民的政治架構後,又廢除越南的科舉制度、進行文化的解構和再建構,以增加殖民體制的穩定度。對越南人來講,若要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就得拋棄傳統的中國式架構、並擺脫新來的法國殖民體制;法國的介入剛好協助越南拆掉中國架構,接下來該做的就剩如何建立越南自己的政治、文化架構。二十世紀初,越南人既然在軍事、政治上暫時無法得到勝利,就應從文化方面下手,透過文化和政治是共生的關係來累積力量。越南的改革派知識份子透過推動越南語文和羅馬字來普及知識、加強民族意識、累積政治反抗的資源;當1945年宣布獨立、建立本土政治架構後,馬上宣布越南語文和羅馬字的國家地位,用政治力來做文化獨立的後盾;透過建造和中國、法國不同的文化架構來確保政治體制的穩定,達成政治、文化的完全獨立。 參考文獻
附錄一 附錄二 1992年4月15日制定,2001年12月25日修訂 第五條
第一百三十三條
參閱Tran, Mong Lang. 2002. Hien Phap Viet Nam: Tu Nam 1946 Den Nam 2001 [Vietnamese Constitution: from 1946 to 2001]. Saigon: NXB TPHCM. 注釋 【1】有關羅馬字在台灣的發展,請參閱Chiung (2001c). 【2】詳細請參閱蔣為文(1997)。 【3】有關漢字的問題,可參閱DeFrancis (1990; 1996)或蔣為文(2001)。 【4】大致相當於當今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島、和越南北部等區域。 【5】今日中國之廣東省廣州市。 【6】「北」指相對越南,位於北方的中國。 【7】原文書名為Viet Nam Su Luoc (越南史略) ,中文版名稱為《越南通史》。 【8】譬如,越南李朝於1075年興建「文廟」(Van Mieu)做為培養儒學人才之官方機構。文廟位於目前河內市「國子監」路(Quoc Tu Giam)。 【9】越南的科舉制度一直延續到1918年才完全廢止。 【10】越南語的構詞法與漢語顛倒,所以「儒字」在越南語裡寫成「字儒」。本文採越語習慣引用越南專有名詞。 【11】根據現存的文學作品年代所論斷。 【12】與Nguyen Thanh Xuan (阮青春)之個人訪談。 【13】與Nguyen Quang Hong (阮光紅)之個人訪談。 【14】有關漢字的缺點,請參閱蔣為文(2001)或DeFrancis (1990)。 【15】有關越南羅馬字的早期發展,可參閱Do Quang Chinh (1972)。 【16】譬如台灣教會羅馬字「白話字 」的發展也是如此。 【17】Thompson (1987:54-55) and Ly (1996:5)。 【18】原文Dictionarium Annamaticum, Lusetanum et Latinum。在越語裡俗稱「Viet Bo La」(越葡拉)。 【19】「得路」的法文名字為Alexandre de Rhodes,越南名字為Dac Lo;「得路」為其漢字名。 【20】Walter Henry Medherst, 1796-1857。 【21】原文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2】有關白話字歷史,可參閱賴永祥(1990)或蔣為文(2001)。 【23】在法國統治時期,雖然在學校有教越南羅馬字,但是它是列在“外文”課程裡教授、且授課時數逐年減少,最後完全用法語上課。(與Doan Thien Thuat之訪談) 【24】台灣府城教會報。 【25】譬如1866年,一位法國殖民地行政官員Paulin Vial在一封信裡提及“From the first days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a barrier between us and the natives…; it is the only one which can bring close to us the Annamites of the colony by inculcating in them 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isolating them from the hostile influence of our neighbors” (quoted in DeFrancis 1977:77). 【26】與Nguyen Quang Hong 之個人訪談。有關「東京義塾」,也可參閱Marr (1971:156-184)。 【27】Hodgkin (1981:288)。 【28】一般來講,“要求已經會某種文字的人轉換到新文字系統” 比“讓「文盲」去接受新文字系統”來得困難。譬如,Stubbs (1980:72)就指出當初美國的英文拼字改革沒有成功的主要關鍵就在民眾的席於陋習而不改變。 【29】這裡所指的台語文指以「 Holo台語」、「客家台語」及台灣原住民語所寫的母語文。 |
 喃」;十六世紀末也經由西歐傳教士傳入羅馬字來書寫越南語。雖然這二種文字很早就出現,漢字在當時仍被越南官方視為唯一正統的書面語。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二十世紀上半段,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法語取代漢文、越南語而成為越南的官方語言。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並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後,他並隨即宣布採用越南語和越南羅馬字為官方語言的政策。自此,越南語和越南羅馬字取代法語、漢字而成為當今越南唯一的口語和書寫語標準。
喃」;十六世紀末也經由西歐傳教士傳入羅馬字來書寫越南語。雖然這二種文字很早就出現,漢字在當時仍被越南官方視為唯一正統的書面語。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二十世紀上半段,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法語取代漢文、越南語而成為越南的官方語言。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並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後,他並隨即宣布採用越南語和越南羅馬字為官方語言的政策。自此,越南語和越南羅馬字取代法語、漢字而成為當今越南唯一的口語和書寫語標準。 喃」或「
喃」或「 」等。據推測,
」等。據推測, 」,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來構成。由於
」,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來構成。由於 」。「
」。「 」(漢越音/le/)用來“暗示”
」(漢越音/le/)用來“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