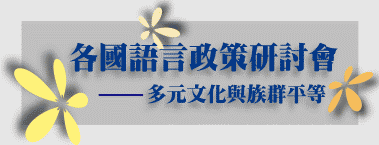
|
|
|
德國語言政策──以索勃人為例 蔡芬芳◎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
|
一、 前言 語言是民族或族群組成的客觀條件之有形特色之一,它亦是最容易與他者區分的特徵。語言最基本的功能是扮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然其所蘊含之更深一層的意義卻往往超越此一簡單的定義;尤其當語言與民族或族群意識結合時,語言所扮演的關鍵性地位將完全表露無疑。語言與民族主義結合的現象係肇端於西元18至19世紀之交的歐洲,時逢「德意志浪漫主義」(Deutscher Romantik)的全盛時期,基於反抗 拿破崙入侵並佔領德意志,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想家、文學家及歷史學家莫不大力頌揚自身的傳統民俗及語言文化,希冀藉此喚醒德人的民族意識及愛國情操,以之作為針對拿破崙大軍佔領德意志的回應。在此種背景下,德語遂獲得德意志浪漫主義文人極度的頌揚與美化,於是語言與民族主義兩者間的結合也就成為此一風潮的產物。德哲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即曾言:「因為每一個民族就是民族,該民 族擁有屬於自身民族的構成要素,一如該民族擁有自身的語言般。」( Denn jedes Volk ist Volk; es hat seine National Bildung wie seine Sprache)。於此不難看出,語言對德意志 民族而言,為界定是否為該民族的重要標準;並且在「解放戰爭」(Befreiungskrieg)擊潰法國佔領軍之後,基於使用相同語言及共同的民族文化為基礎而引發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浪潮,對於往後德意志統一國家的實現具有極為關鍵性的地位。由上述例證觀之,語言對於德意志民族而言,實已轉化為帶有政治意涵的「民族語言」。【1】 自西元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赫德、費希特 (J. Fichte,1762~1814)及溤•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中可看出,語言對於德意志民 族的意義在於語言是延續民族及國家的文化與命脈,祖先語言之重要性,世間無任何事項可堪比擬(愛德華滋1994:35~40)。尤有甚者,費希特且認定德意志民族保留自身語言之原貌,未受到其他語言的滲入及影響,所以德語遠優於其他的語言,因此之故,德意志民族及國家亦較之其他民族與國家更為優秀。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費希特的論點實係無稽悖理,然它卻展現出語言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Edwards 1995:131)。 就上述德意志文人思想家對德語價值的闡釋,不難窺見出德語對於德人所蘊含的 崇高意義。如此心態,亦反映於德國人面對國內原生(autochthon/ansässig)少數民族(die nationale Minderheit)時的處理態度上。德國基本法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中並無任何針對德國境內少數民族權益之相關條例,更遑論語言政策方面的規定,德國境內少數民族相關權益之規定僅散見於各邦憲法之中。然諷刺的是,德國政府卻竭其心力地為散居於德國本土之外,尤其是世居於中、東歐諸國的德意志民族爭取其於所在國應享有之權益。再就德國基本法相關內容觀之,亦可窺見德國憲法對德境少數民族的漠視;基本法序言卻僅以德意志民族(das Deutsche Volk)來指稱基本 法權利義務規範的對象,第116條第一款所定義之「德國人」【2】,係指涉擁有德國公民身份者(di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besitzt)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中東歐各國強行逐出的「德裔難民」或「德裔被驅逐者」【3】(Flüchtling oder Vertriebener deutscher Volkszugehörigkeit),而對於世居德國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之稱謂則隻字未提。 面對德國基本法對於德國境內少數民族有意無意的忽視,這些少數民族觀感為何 ?並應如何維護自身語言文化於不墜?頗值得吾人作深入之觀察;另外在各邦憲法架構下的語言政策對於攸關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語言維繫及發展有何影響,亦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擬以德國境內屬於西斯拉夫民族之原生少數民族―索勃人(die Sorben)為 主題來探討德國語言政策。在進入正題之前,首先當然有其必要針對德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或族群略作概觀,以期對德國族群結構有所瞭解。 二、德國族群結構 德國總面積為357,020.22平方公里,根據西元2000年統計,人口總數為82,182,824人,其中91%為本國人,9%為外籍人士。德國境內除了主體民族德意志民族之外,其他少數民族可分劃為三:首為原生少數民族;其次是外來移民;第三類尚在討論當中,但已有學者提出―西元1989年/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前東德五邦(Bundesländer)【4】的人民是否可被視為一個族群(ethnische Gruppe)(Howard 1995: 119-131)?現分述如下 。 (一)原生少數民族 分布在德國境內的原生少數民族,除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分布在德國東部並與 捷克人、波蘭人血緣相近的索勃人以外,還有居住在德國北部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 (Schleswig-Holstein)的丹人(Dänen)、弗利斯蘭人(Friesen)【5】以及散居德國各地的辛提人 與洛瑪人(Sinti und Roma)。 丹人與德國其他的少數民族的最大不同處在於他們有丹麥母國做為他們強力的後盾,而這對於他們語言及文化的維持及發展有相當大的優勢。現今約有五萬名丹裔德人定居於南什列斯威(Südschleswig)。至於德國丹裔少數民族的問題早自德意志第二帝國締建之前即已出現;西元1864年丹麥王國片面合併當時屬於「德意志邦聯」(Der Deutsche Bund,1815~1866)的什列斯威-霍爾斯坦聯合公國,此舉引發德境各邦強烈不 滿,因而德意志雙強-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對丹麥作戰,並將之擊潰,乃將境內擁有許多丹裔的什列斯威併入德意志邦聯,其後並成為西元1871年所締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之組成一部。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境丹裔少數民族問題再次浮現;為了徹底解決德國與丹麥之間因少數民族所引起的領土爭議,戰勝國遂援引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所提倡的「民族自決原則」(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Völker)以及西元1919年所簽訂的凡爾賽和約(Versailler Vertrag)的第109條「德國與丹麥 的疆界由人民來決定」,乃於西元1920年在什列斯威舉行公民投票。公投結果,南什列斯威的居民高達70%以上願意繼續留在德國。與之相對的,在現今丹麥境內的北什列斯威(Nordschleswig)的居民則選擇歸屬丹麥,因此丹德兩國境內互有德裔丹裔少數民族居處。自西元1955年起德國與丹麥之間正式建立對話管道,俾保障彼此留在對方國內的同胞之語言與文化等相關權益。 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可謂之為德國各邦中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一邦,該邦不僅 擁有丹裔及弗利斯蘭人兩支少數族群,而且共有五種語言通行於此:標準德語(Hoch-deutsch)、低地德語(Niederdeutsch)、丹麥語(Dänisch)、北弗利斯蘭語(Nordfriesisch)、南朱特語(Südjütisch),因此該邦憲法對於少數民族及其語言的保障自不得不有所著墨。在該邦憲法條文中,對於攸關少數民族權益的保障可見之於有關學校教育部份;該邦憲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負有教養責任者或監護人可自行決定,其子女是否應進入少數民族之中小學接受教育」。【6】 由於上述邦憲法條文的保障,使得居住此邦的丹裔少數民族的權益基本上能獲得 許多保障。當然丹裔除了倚賴自身之力以追求自身族群的權益外,亦與該邦另一少數族群-弗利斯蘭人相互合作以匯集群力;例如全權負責該邦丹麥語學校教育的「丹麥語學校協會」(Der Dänische Schulverein)即清楚表明與同樣分布於該邦的弗利斯蘭人共 同合作。他們首要關注的要務當然在於傳承自身民族的語言文化,與此同時兩族群亦教導學生身為德國公民的少數民族身份。 不過在此尤須一提的是,丹裔與弗利斯蘭人在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邦憲法(1990) 中的地位並不相同,該邦憲法第五條明載丹裔為「丹麥少數民族 」(die nationale dänische Minderheit),而弗利斯蘭人則僅為「弗利斯蘭族群團體」(die friesische Volksgruppe);該條文意謂著弗利斯蘭人並不被認可為少數民族的地位。因此弗利斯蘭人不僅在整個德國大環境中處於邊緣地位,甚且被歸列至丹裔少數民族內部的次級團體之中。因此弗利斯蘭人沒有完全教授自身母語的幼稚園及中小學,而僅能與丹裔合作(POGROM 1994:15~16)。在此種不利大環境的外在條件下,為了維繫自身文化傳統 於不墜,他們只能先從強化母語教育的措施著手。目前在北弗利斯蘭語通行地區的各級中小學皆提供每週兩小時的母語教學,學生可自由參加。 此外,丹裔少數民族及弗利斯蘭人皆有所屬推動各自母語及文化保存的組織。丹裔的總樞紐組織為南什列斯威協會(Sydslesvigsk Forening, SSF / der Südschleswigsche Verein, SSV ) ,而弗利斯蘭人則有北弗利斯蘭研究所(Nordfriisk Instituut),其宗旨是為 保護、促進及研究北弗利斯蘭語言與文化的學術機構。尚須一提的是,上述兩族群文化組織皆與歐洲層級的機構密切合作,例如歐洲族群團體聯盟 (Föderalistische Union Europäischer Volksgruppen, FUEV)及歐洲少數語言總署(European Bureau for Lesser Used Languages, EBLUL),此舉有助於他們語言與文化生命的延續。 居在德國境內已逾六百年以上的「辛提人與洛瑪人」,即一般人所泛稱的「吉普 賽人」(Zigeuner/Gypsy),然此種稱謂隱含歧視性的意味,其意實與「小偷」或「天生竊犯」等同。據學界估計,今日全球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的辛提人與洛瑪人,其中四百萬散居於歐洲各地,近八萬人居住在德國境內。納粹掌權時期辛提人與洛瑪人亦如猶太人般慘遭迫害及屠殺,時至戰後該族群地位仍備受歧視,甚且被取消國籍,成為無國籍之民。與其他德國原生少數民族之最大不同處在於辛提人與洛瑪人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地位,因此希望德國政府認可其為少數民族是辛提人與洛瑪人的最主要訴求。 (二) 外來移民 德國外來移民的出現,始於西元1960年代初期。時逢西德經濟奇蹟年代,因國內 勞力不足,故從土耳其與南歐國家引進大批外籍勞工(Gastarbeiter)。依西德政府的最初計畫,外籍勞工居留德國有其限期,並非永久居留,然而隨著時間之演進,此類外籍勞工不僅在德國安家立業,而且要求取得德國國籍,遂成德國內政上一大難題。此類外籍勞工為數最多的是土耳其人,總數近兩百萬人之譜【7】。土耳其人移民德國,可分為三個階段:西元1960~1973年為年輕的土耳其勞工獨身來德;第二階段是自西元1967到1980年代初期,原在德工作的土耳其勞工將土耳其的家人接到德國同住;第三階段則為土耳其人開始在德國安家立業並同時建立他們自己的社區(Ertekin Özcan 1995:513-515)。有關土耳其人的母語傳承方面,土耳其孩童除了一般正規課程之外,學校亦提供母語課程,各邦規定不同。在土耳其人人數最多的北萊茵-西發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土耳其語不只是母語課程,更被列為第二外語的選修課程之一,同時大學中亦提供教授土耳其語的師資養成教育班。 德國另外一批主要的外來移民則是來自共黨政權垮台之後的前蘇聯及前東歐共產國家(尤指波蘭與羅馬尼亞)的「德裔回歸者」(Aussiedler),據統計從西元1990~1999年共移進 2,029,176人,其中來自前蘇聯的德裔高達1,630,041人(Der Spiegel 4/2001:56)。 但是事實上70%來自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俄羅斯的所謂德裔移民並非真正具有德意志民族的血統。因此近年來,德國國內各政黨皆要求嚴格調查德裔回歸者是否真正擁有德裔血統。並且即令真正具有德裔血統者,德國政府亦要求必須能操德語,以利整合至德國的「主流文化」(Leitkultur)之中 。 現今仍在德國國會(Bundestag)中討論的「移民法」(Zuwanderungsgesetz)亦將德語能力視為外來移民融入德國的關鍵要素之一。例如過去的外來移民只需簡單的口語溝通能力即可,但若「移民法」通過後,移民者必須通過德語語言測驗,意即必須同時具備德語聽說讀寫能力。 (三) 前東德五邦人民是否可被視為一個族群? 西元1990年10月3日兩德正式統一,然在興奮之情消退後,德人面對的卻是現存許 多棘手難解的經濟及社會問題,由於兩德政經社結構的極大差異,使得德國統一後,為了調合德國西部及東部個人所得及各方面的巨大落差,導致德國政府必須加稅以因應前東德地區各項基礎建設之所需。時日既久,德西民眾不免怨聲載道,質疑德國統一的代價過鉅,並強烈不滿將大筆資金投入德東地區,而使德西生活水準更進一步提高的希望為之停滯不前;德東民眾同樣不滿,指陳德國統一後,使德東失業率屢創新高,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即東德共黨)統治時期的全民就業時代已然不復可尋。在此種德國東西部民眾對德國現狀皆失望的情緒下,導致德國東西部相互不滿之心與日俱增。許多學者因而不禁提問:柏林圍牆倒了,然德東及德西民眾間那堵無形的牆是否亦為之崩塌消失?Howard(1995)認為,雖然東西德民眾不因語言、宗教【8】及種族而有所區別,然對德東民眾而言,更重要的是德東民眾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價值觀、奮鬥歷程,共享榮耀、尊嚴【9】(Ehr-und Würde-Gefühl),以及可資區別他者的「我們」意識(Wir-Bewußtsein)。若依此種觀點而論,則德東人民實可被視為一個族群。由此一論點出發,將有助於瞭解東西德民眾思維及行為模式等各方面的差異【10】,而且對於今日德國現存的各項社會問將是一個極佳的分析切入點。 三、誰是索勃人? 那麼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德國將會是另一番新面貌【11】 Jurij Brěsan【12】 一語道盡索勃人在德國的心聲 - 雖與德意志民族立足於同一地面上達千年以上, 然而在漫漫長河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索勃民族始終面臨著強大德意志民族的同化-「德意志化」(Verdeutschung/Eindeutschung/Germanisierung)的壓力。時至今日,儘管索勃人的語言及文化保存了下來,但期間歷程卻是艱辛萬分。究竟這千年之中索勃人與德意志民族間的互動關係為何,索勃人如何承受強大的德意志化的壓力卻仍能維繫其語言文化於不墜。在本文析論有關德國薩克森邦及勃蘭登堡邦邦憲法條文中對索勃人語言的維繫及保障之前,實有必要先行回顧索勃人與德意志人千年的互動歷史,藉以明暸本文主旨之所在,並進而知悉今日索勃人所面臨的各項困境之所由;其次析論索勃人內部差異,以明白今日索勃人內部各方面自我認同的歧異。 (一)歷史背景 索勃人為今日德國東部,即前東德境內的一支少數民族,據統計其人口總數僅存約六萬人。根據人類學家與語言學家的考證結果,索勃人是屬於斯拉夫人種,其語言亦屬斯拉夫語系,這與該族群今日所歸屬的德國主體民族及其語言-日耳曼人種的德意志民族及所操之德語,皆差異甚遠,反倒與其鄰近的三個斯拉夫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波蘭、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居民血緣相近,然而何以今日索勃人只是德國境內的一支斯拉夫少數民族,而未像其他三支斯拉夫民族般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國度,這當然涉及到中歐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結果。 索勃人居於德東地區至今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若稱其為德國東部的原住民絕不 為過。索勃人遷徙到德東實與東歐上古中古之交的歷史事件息息相關;當西元4~5世紀「民族大遷徙」(Die Völkerwanderung or Movement of Peoples)運動展開之後,隨著日耳 曼諸部族西向南向遷徙風潮席捲而去後,緊隨其後亦有西元6~7世紀的斯拉夫民族遷徙擴張運動(圖1),當時斯拉夫民族由其原始起源地普里配特沼澤區(Die Pripet-Sümpfe or Pripet Swamps)分向東、西、南三方前進,其後在人類學及民族學上乃分別被歸類為東 、西及南斯拉夫人種。西斯拉夫人的遷徙路線朝向中歐,他們約在西元600年前後,向西推進到今德國境內的易北河(Die Elbe)及其支流薩勒河(Die Saale)與波希米亞森林(Der Böhmerwald or Bohemian Forest)一線,當時居於西斯拉夫民族最前端的部族即索勃人 ,即德文文獻上所稱的「溫德人」(Die Wenden)【13】。由於當時他們散居於德境易北河及 其支流薩勒河流域一帶及以東之地,並分為多支不同的部落,因此德人亦將之稱為「易北河斯拉夫人」(Elbslawen)。不同於其血緣相近的兄弟民族波蘭人及捷克人分別於所居之地逐步匯集各部落而建立初步的國家組織,索勃人至10世紀之時仍維繫著鬆散的部落同盟形式,在此種背景下,索勃人致而陷入四鄰諸國,尤其是西鄰的德意志民族的窺伺覬覦之中,並自此之後步上了悲慘的歷史發展。自西元10世紀初開始,德意志王國及其後的德意志第一帝國(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在君主亨利一世(HeinrichI.919~936)及其子鄂圖一世(鄂圖大帝)(Otto I. der Große,936~973)的統治下,展開了「東向政策」(Die Ostpolitik),開始進行征服易北河以東之地,並對當地進行基督教化之舉。 當時是歐洲基督教信仰定於一尊的年代,基督教傳播是透過「火與劍」(mit Feuer und Schwert)來達成的,其過程甚為殘酷,許多堅持原始傳統宗教信仰的索勃人被殺 被逐,自此之後,索勃人遂被迫逐步接受了基督教。然而儘管索勃人臣服於德意志皇權之下並接受了接督教的信仰,但索勃人在易北河以東之地仍能維持多數民族的地位。然自西元12世紀開始,因德境西部人口成長壓力及中東歐各諸侯國為求境內開發而大舉招徠德意志移民移入的背景下,大批德意志民族移向中東歐地區,此即第二波「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Die deutsche Ostsiedlung)運動【14】;其時索勃人所居之地首受波 及,除了今日德國東部的勞席茨(Lausitz or Łužica or Łužyca)地區(圖2)索勃人仍能維繫人口上的多數外,其餘地區皆在其後數個世紀內全部被「德意志化」,即令在勞席茨地區,索勃語亦備受打壓,例如許多城市法院中禁止使用索勃語,使得索勃人及其語言陷入德意志化的危機中。西元1519年德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對於索勃人而言有著雙重的意義:一方面由於這項運動之故使得索勃人的民族特性得以維繫,係因索勃神父雅庫必查(Miklaws Jakubica)在西元1548年翻譯了新教路德派聖經,從而創造出索勃文,索勃文的問世,使索勃人終有了形之於書面的文字,其特有的文化傳統遂得以藉此而傳承不墜。另一方面雖受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使大部份的索勃人都皈依新教,但位於上勞席茨(Oberlausitz)的小部份索勃人則仍維繫原有的舊教天主教的信仰,也因此造成了索勃人宗教信仰的分裂。 西元1618~1648年的歐洲三十年戰爭(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期間及緊隨其後爆發的瘟疫,索勃人受創甚重,其人口總數在此期間劇減一半以上,使得索勃人的領域及語言的分布區域更是大幅縮減。其後西元17~18世紀時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Das Haus Hohenzollern)勢力迅速崛興,並與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Das Haus Habsburg)及其盟友薩克森威廷家族(Das Haus Wettin)展開激烈對決,夾處於其間的勞席茨地區索勃人遂再次受到嚴重的打擊,尤其在維也納會議(Der Wiener Kongress,1815)結束普魯士王國逐步得勢以後,向來對索勃人嫌惡不已的普魯士王國更對之展開大規模同化政策,然此舉適得其反;在西元19世紀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中,許多索勃詩人、文學家及音樂家創作了大量的詩篇、文學作品及民族音樂,並成立了許多索勃文化協會,以之作為針對普魯士王國同化政策的一項回應,藉此並進而達到了索勃文化的全盛期。 西元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正式成立之後,仍企圖對索勃人採取全面同化政策,但索勃人無畏其壓力,持續發揚其特有的文化;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於1904年成立的「溫德人之家」(Das Wendische Haus)及1912年的「家園」(Domowina),這對索勃人產生了極大的精神鼓舞作用,象徵著索勃人對維繫自身文化及語言的強烈意念。 威瑪共和時期及其後的第三帝國時期,索勃人的處境更形惡化。尤其納粹政權基 於種族優越的理念,向來視斯拉夫人為「次人」(Untermenschen),因此對於德國境內的斯拉夫索勃人自是憎惡萬分。此種背景下,索勃人的傳統文化遭受全面的打壓,公開場合禁止使用索勃語,大批索勃菁英、領袖及教會人士被集體遣送集中營,甚至遭暗中處決。直到納粹崩潰後,幾乎被摧殘殆盡的索勃文化及語言方才重獲生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索勃人面臨了與其斯拉夫兄弟民族的波蘭或捷克合併或是留在前東德境內的考量,但最後索勃人決定留在前東德境內。這主要係取決於前蘇聯政府的態度,因為史達林欲維繫其所掌控的「東方集團」(Ostblock)各衛星國中的實力平衡,不願波蘭或捷克的領土過度擴張。其次前東德政府為籠絡索勃人而賦予其政經社及文化、語言等的各方面的平等權利,並明文規定於東德憲法條文之中。然就實際層面而言,雖然前東德政府賦予索勃人各項平等的權利,但這些措施並未實質改善索勃人在前東德社會中的各項困境,索勃人仍感受到身為少數民族所遭到的若有似無的歧視。兩德統一之後,索勃人一度對自身民族文化與語言維繫的前景抱持樂觀的看法,然隨著德國國會於西元1994年否決了少數民族法案之後,似乎註定索勃人仍難脫悲情的宿命,今後可想得見地索勃人仍將為自身所屬文化及語言的存續持續奮鬥。 (二)索勃人之「內部差異」(interne Differenzen) 「內部差異」一詞在此具有雙關意義,一為外界如何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觀察索勃人,另一則是索勃人本身有其「自稱」(Selbstzuschreibung)的及語言、宗教、認同方面的差異。 簡而言之,若就傳統文化概念的角度來觀察索勃人,則外界人士自然會將之與其他民族或族群做一明顯的區別(Abgrenzung),並認定其生活領域及活動範圍集中於勞席茨地區,而且也會使用「索勃人」一詞來指稱所有的索勃人。此種外在對於索勃人的看法,可說是以「同質化」(Homogenisierung)的眼光來觀察索勃人。但是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文化並非一成不變,靜止不動。在今日文化全球化(kulturelle Globalisierung) 的衝擊下,原來的文化、生活方式及思維模式,很難不受到外來的影響,因而產生「混合的」(Vermischung) 、「混雜的」(hybrid) 、「牛奶咖啡效應」(Melange-Effekt)【15】以及「網絡交織世界的文化」(Kultur in einer vernetzten Welt)(Hannerz 1995)等現象。因此「文化」(Kultur)不再以單數的形式出現 ,而是複數的「文化」 (Kulturen)。此外 ,由於經濟活動的國際化、無遠弗屆的媒體傳播、電腦網際網路的發達、交通往來的便捷以及世界上因移民、外籍勞工、難民或是觀光客等因素所造成的人員流動,都會產生移動性(Mobilität)的現象,使得「文化」因此不再侷限於某地,而呈現出跨文化(transkulturell)及跨國界(transnational)的情形。 基於此種轉變,若再以「同質化」或者「本質化」(Substanzierung)的觀點來觀察或研究一個文化、民族或族群時,則難以避免地會忽略他們個中所存在的差異性與個體性。換句話說,今日若觀察研究一個族群及文化時,應以「異質」(heterogen)及「多重」(multipel)的角度出發,否則恐將陷入「同質化機制」 (Mechanismus der Reinigung) (Tschernokoshewa 2000:85)的陷阱之中。因為在「同質化」的框架下,文化、族群、 民族、國族、國家及個人全部被歸結(gekoppelt)在一起【16】,而無所區別,唯一的差別僅在於與「他者」(Fremde)間的不同,「他者」因此被邊緣化、被忽略甚至被消滅(Tsch-ernokoshewa 2000:66-69)。今日索勃人在德國的處境,即是作為德國主體的德意志民族眼中的「他者」,在德人強調並希望擁有德意志民族的「純度」(Reinheit)的同時,索勃人遂因而被排除在外。 另外,使用「異質」的觀點來進行觀察亦將有助於我們不再帶有「偏見」來看待其他文化,或不再將「他者」的行為模式套入陳腔濫調的邏輯中,如此才能更進一步地增進彼此的瞭解。例如並非所有的索勃人都過著以農為務的生活,而索勃婦女亦非一如介紹索勃文化書冊所呈現的終日僅著傳統服裝之形象,實則索勃人有其真實的生活型態。 第二個「內部差異」則指索勃人本身如何「自稱」及索勃人內部的語言、宗教及認同等各方面有何不同。但在此仍須再次強調的是,「索勃人」是一個總括的概念(Oberbegriff),卻不能因此而忽略他們個別的主體性。 首先就索勃人的「自稱」而言,索勃人的主要居住地區為德國東部的勞席茨地區,其中又分上、下勞席茨。而索勃人也因此而被區分為上索勃人(Obersorben)及下索勃人(Niedersorben)。但是就索勃人的稱謂而言,則必須區別「溫德人」與「索勃人」的不同。可分兩個層次:一為「溫德人」主要是德意志民族對他們的稱呼,即所謂的「他稱」(Fremdzuschreibung),而「索勃人」則為「自稱」。二是上、下索勃人採不同的「自稱」,上索勃人稱自己為索勃人,然而下索勃人則自稱為溫德人,其因在於在前東德時代,上索勃人與當時執政的東德共黨關係密切,因而引起下索勃人對上索勃人心生不滿, 因此下索勃人乃自稱溫德人,藉著不同的稱呼來區分下索勃人與上索勃人間的不同。 其次就索勃語(Sorbisch)的差異而言,亦因上下勞席茨地區之不同而分為上索勃語(Obersorbisch)及下索勃語(Niedersorbisch),其中上索勃語近似捷克語,而下索勃語則和波蘭語相近。原本索勃語中存有許多地區性語言,直到西元19世紀中期,才將包岑(Bautzen/Budyšin)與寇特布斯(Cottbus/Chośebuz)的地區語言升格為通行上、下勞席茨地區的上、下索勃文的口語與書面的標準用語(Elle 1995:462)。上下索勃語不論就書寫形式及口語用法上都存有些許差異。另由於索勃人與德意志民族接觸已歷千年以上,所以索勃語可被視為斯拉夫語系與日耳曼語系結合的最佳產物,因為作為西斯拉夫語系一支的索勃語,不論在字彙或文法上都受到了德語的外來影響。【17】 最後就宗教差異而論,自西元968年麥森主教區(Bistum Meißen)的設立後,德意志 境內的基督教會及王室諸侯開始東向對索勃人進行了以武力為後盾的傳教使命,索勃人雖屢經抗爭,然終不敵這股強大的基督教化壓力,此後數世紀之內,索勃人遂被迫全面皈依基督教。不過索勃人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在西元16世紀初的宗教改革運動後,出現了分裂的情形;在上勞席茨地區的包岑、卡門次(Kamenz/Kamjenc)及豪雅斯維爾達(Hoyerswerda/Wojerecy)三城市間所構成的三角地帶內的索勃人仍維繫原有的信仰天主教,其餘則全面改宗基督新教路德派。因此在這塊三角地帶之中信仰天主教的索勃人居於「雙重少數處境」(doppelte Minderheitenposition)之中―一方面他們處於強勢的 德意志民族的影響之中;他方面則同時必須面對信仰基督新教路德派的索勃同胞;然而居處這片三角地帶的索勃人卻憑藉著天主教信仰為依歸,並以之作為索勃人自我的強力認同後盾(Toivanen,2001:46)。今日不同的研究的結果皆顯示,天主教索勃人聚集區實為索勃文化的傳承及發揚的核心地區(Elle,1992:49)。就族群及文化的認同來說,天主教上索勃人是最強的,其次是上勞席茨其它地區的上索勃人,至於下勞席茨的下索勃人自我族群及文化認同感較為薄弱,這亦連帶影響到索勃語的使用情況。索勃民族中的菁英份子一再地強調語言是索勃人認同的核心要素(Elle,1992a;Tschernokoshewa(Hrsg.)1994:105);因此上勞席茨地區的上索勃人,特別是三角地帶信仰天主教的上索勃人使用索勃語的頻率遠較下勞席茨地區的下索勃人高出甚多。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下勞席茨地區的索勃語言及文化的流失是因工業化所造成的;自西元19世紀中葉以降,時逢當時的普魯士王國及後來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正全力推動國家工業化的措施,由於位於普魯士王國領域內的下勞席茨地區發現蘊藏大量褐煤,因而普魯士王國及第二帝國政府乃在當地大肆推動煤礦工業,以致遂有大批德國人移入下勞席茨地區以充任礦工。德人的大舉移入使索勃人又再次面臨德意志化的危機(Kunze,2000:46~47)。自西元20世紀初始,下勞席茨地區約有113個村莊被強制遷村,遂導致該地的索勃人數在當地人口結構迅速下降,時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東德社統黨政府掌權後,此一局面仍持續惡化,總計自西元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原佔有三分之一的索勃人口降為六分之一,而這對下勞席茨地區索勃文化的保存無寧是一大戳傷(Toivanen 2001:36)。 四、關於德國的索勃語言政策 仍遭忽視如故,反愈形步向衰亡之途。【18】 Roža Domašcyna 兩德統一之後,索勃人對於該民族在德國法律地位的改善又燃起了一線希望,他 們樂觀地認為「我們在新的德國社會中看到我們民族的未來…索勃人的民族權利可以獲得絕佳的實現機會」(Kasper1995:41),然最後結果卻是再一次遭受打擊。原本兩德政府在統一前曾表明在統一後兩年之內,將增修德國基本法條文列為首要工作之一。其中最為攸關德國境內各少數民族者,莫過於基本法中欠缺少數民族的保護條例,因此包括索勃人在內的德境各少數民族莫不殷殷垂昐德國基本法中能增列保障少數民族權益的條文。然而西元1994年7月30日德意志聯邦國會中多數的國會議員卻否決了少數民族條例,此項決定不僅令德境內索勃人、丹人、弗利斯蘭人及辛提人與洛瑪人極感錯愕不滿之外,相關國際組織,如歐洲族群團體聯盟、歐洲少數語言總署及國際民族權利暨區域主義研究所(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ür Nationalitätenrechte und Regionalismus, INTEREG)亦對居歐洲聯盟(Europäische Union,EU)龍頭老大地位的德國如此忽視境內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感到失望不已。 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德人對於少數民族或族群語言的忽略,非始於今日,本文前面篇章已然詳述歷史上各時期德意志人對索勃人的同化措施,姑不論中世紀民智未開、尚未產生尊重相異族群文化及語言觀念的年代,時至近現代,德人對於少數民族的語言及文化態度似仍未有太大的改變,本文以下擬由有關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在德國的出現開始,析論德國各時期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制定、演變與缺失,將有助明暸德國國會否決少數民族條例之因。 (一)自西元1849年國民議會憲法至西元1945年納粹政權覆亡止 索勃人的語言權益問題來說,可追溯到1849年於麥茵河畔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保羅教堂所舉行的國民議會憲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中的第188條「確保德國境內的非使用德語民族的發展,意即此類民族所操之語言及其於教會、學校、內部行政及權利保護等皆享有平等地位」【19】。然就實際層面觀之,此項條文並非真正以平等地位對待德意志境內操其他語言的少數民族,實則對少數民族的權益多所保留,且只有在少數民族聚居分布的領域之內才能享有某種程度的權利。當時索勃菁英人士即曾致書國民議會中民主派領袖Robert Blum,要求索勃人在德國社會中應享有平等的各項政經社權利;但所得到的回答竟是:「國民議會已注意到你們的需求,你們的請願在不久的將來可獲實現」(Elle1994:82),德人漠視少數民族權利的心態由此可見一斑,民主派人士已然如此,更遑論其後的充滿帝國主義擴張野心的第二帝國民族主義人士。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西元1919年所通過的威瑪憲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第113條的規定「德國境內操他種語言的民族允其自由發展,尤其在學校、內部的行政及權利保護方面時母語的使用不得受到妨礙」【20】。但首先索勃人認為該條文中的「操他種語言之民族」定義不清,所指的究竟是所有非以德語為母語的少數民族,或是無法說德語的民族;因為部份索勃人已然完全被德意志化而以德語為母語,但大部份則仍操索勃語,因此牽涉到主觀與客觀認定的問題(Pastor1997:27-28)。其次,雖然威瑪憲法中亦顧及德境內少數民族的權益,但是條文中的「不得受到妨礙…」的隱含意義則是國家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發展無意承擔任何義務,而僅採包容的態度對待之(Pastor 1997: 26)。因此該條文內容形同具文 ,毫無實質意義。 德意志第三帝國納粹時期是全面禁止任何與索勃文化有關的事務,可謂索勃人處境最艱難的時代。納粹政權為求徹底將索勃人德意志化,除了大肆逮捕索勃菁英外,更是硬生生地將索勃人套入德意志民族的框架之中,並藉由學術研究成果抹滅索勃人為斯拉夫民族的事實:「索勃人具有北歐亞利安-日耳曼人種的外形特徵,他們的傳統服裝及風俗習慣毫無疑問地為德意志式的,而索勃人之所以操著屬於斯拉夫語系的母語,係因其本來為日耳曼民族的汪達爾人(Vandalen)遷往南歐及北非後留在中歐地區的剩餘族群,其後因經歷了灰暗的先古時期「劣等」(Schwäche)斯拉夫種族的入侵中歐,他們才被迫轉操斯拉夫方言(Oschlies 1991:29) 」。秉此可見,索勃文化及語言在納 粹時期幾遭消滅,遑論任何有關索勃語言政策制定的可能性。 (二) 前東德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第三帝國的戰敗及歐洲政治局勢的改變,德國分裂為二,索勃人被納入了蘇聯卵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前東德)而淪入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ED,即共產黨或簡稱社統黨)的統治之中。此一時期有關於索勃人的語言政策是涵蓋在主政的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所制定的「民族政策」(Nationalitätenpolitik)之內。然而「語言政策」一詞並未出現在所謂的「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之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政策」(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Nationalitätenpolitik der SED)中。所謂的「民族政策」根本 僅是東德社統黨的中央委員會以及政治辦公室的領導人憑其主觀意見而專斷決定的(Elle,1995:11)。 就索勃人而言,索勃語的傳承是維繫索勃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他們最關切的是學校教育中的索勃語的地位以及公開場合的索勃語使用情形。索勃菁英在西元1946年於羅迪勃(Radibor/Radwor)設立第一所索勃語教師學院(Sorbisches Lehrerbildungsinstitut),以培養學前教育及中小學教授索勃語的師資。為了收攬索勃人心,前東德社統黨政府當然以提升索勃人的文化及語言地位為號召,然而綜觀前東德社統黨政府於西元1949年10月7日所頒布的東德憲法中有關於索勃人的第11條【21】之相關規定,可說了無新意,因為該條款幾乎完全抄襲威瑪憲法第113條而來。以致儘管前東德時代勞席茨地區的各級學校中皆實施雙語教育、並成立為數不少的索勃文化機構,而且街道與公共設施亦設置雙語標示,但最終索勃人仍脫離不了社統黨政府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而迫使其與前東德社會一致化(gleichgeschaltet),以致索勃文化及語言根本無法蓬勃發展。Elle(1995)將前東德時期關於索勃人的語言政策分為如下三階段:西元1948~1954年;1954年~1958年;1959~1989年,以下分述之。 1.西元1948~1954年 西元1945~1948年間,前東德社統黨政府並未提出任何有關索勃人的權益法案,第一個針對索勃民族的權利條文「索勃人法」(Sorbengesetz)反而是誕生於西元1948年通過的薩克森邦邦憲法,該邦憲法同時也是德國第一個較具雛形的揭示有關少數民族權利規定的邦憲法;內容中有關維繫語言方面的條文側重於中小學以索勃語為教學語言;索勃語可通行於行政機關;公共標誌雙語化。繼薩克森邦邦憲法之後,前東德憲法及勃蘭登堡邦邦憲法才分別於西元1949年及1950年明載有關索勃人權利條文的相關規定。 這段時期強調的是以索勃語為主的學校教育,因此索勃民族教育部門(Sorbisches Volksbildungsamt)乃於西元1948年成立,但實則該部門的實際運作延宕數年之久。其因是社統黨政府領導人認為,為索勃人培育教授索勃語的師資或者設立索勃語學校等措施,耗費國家成本過多,而且此舉只是用人為的力量硬將一個行將大限的文化及語言提昇起來罷了,實不符東德國家的實際利益。社統黨政府的此種心態說明了社統黨政府並非真正有心保護並促進索勃語言及文化的發展,因此社統黨政府當然也就無心安排足夠且適合的人員來負責索勃人之相關事務。 2.西元1954~1958年 在索勃人聚居的勞席茨地區推行雙語措施為此一階段的特徵。前東德政府規定在公共場所採雙語並行標示-包括郵政、電話簿、火車站標誌等,並規定勞席茨地區的公務員應學習索勃語。然儘管前東德社統黨政府制定了為數可觀的條文,實際上卻並未完全執行。從西元1956~1958年終於有些許作為:西元1956 年索勃民族藝術之家 (Haus für sorbische Volkskunst) 成立;索勃語廣播節目開播;下索勃語週刊「新報」 (Nowy Casnik)創刊 ;1958年家園出版社 (Domowina-Verlag)成立;西元1956年並設立 欽緒斯基獎(Ćišinski-Preis),俾表揚為索勃語言及文化的提升作出貢獻的人士。 索勃人甚為重視的索勃語教學課程在此一階段中根本未見實現,因為有關學校中實行索勃語課程的民族教育部長會議從未召開。而行政機關中索勃語通行的相關規定亦形同具文,完全不見公務機構中有任何操索勃語的公職人員來服務索勃人。基於上述現象,Elle(1995:49)因而認為此一階段的雙語政策是全由社統黨政府高層單方面決定的,並且本質上根本是一項毫無事先周密規劃的語言政策。 3.西元1959~1989年 Elle(1995:51-52)總結自西元1959年之後前東德政府針對索勃人而制定的語言政策中,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1)先前由西元1945~1958年間前東德社統黨政府所推行的各項針對保護索勃語的措施,幾無成效可言,淪為紙上談兵。 (2)儘管勞席茨地區美其名為德語及索勃語雙語並行地區,但其間並無完善規劃及執行具體保護索勃語的措施。時至西元1982年時設立索勃電影及紀錄片製作團隊;至西元1989年擴充索勃語發聲的廣播節目時段,情況才稍見改善。 (3)就整體而言,前東德政府有關保護與促進索勃語發展的「民族政策」流於形式,而且社統黨政府將所制定與執行的語言政策套進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框架中,並使之淪為社統黨政府籠絡索勃人,並藉之換取索勃人交心的工具。 (4)自西元1962~1964年間,索勃語的教學品質無論就質與量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缺失:學生的索勃語程度不佳而且參與索勃語課程人數持續下降。 此一階段的三十年之間,對索勃語教學的最大負面影響係來自於前東德政府的學校教育政策的改變。原本自1952年開始設立的所有科目皆以索勃語進行教學的A型學校(A-Schule)中,到了西元1962年,前東德政府突然宣佈所有與自然科學相關科目皆不再以索勃語進行教學。然此一聲明並沒有依據任何客觀的調查及分析來說明學生以索勃語學習自然科學的成果為何,只有前東德政府官方片面的說法:「以德語學習現代科學與技術,學生能獲得較良好的成績,同時有助於將來職場發展」。社統黨政府甚且指出,有些村莊希望廢除A型學校,認為只要有索勃語被視為「他種語言」(Fremd-sprache),一週約三小時課程之B型學校(B-Schule)即可,希望獲得外界支持其廢以索勃語教授自然科學學科的計劃。然而為時不久,前東德政府竟然進一步將A型學校廢除,此舉足以證明前東德政府根本無心投注心力於索勃語的維繫上。甚至到了西元1964年,前東德政府連B型學校的索勃語課程也欲廢除,其對外說辭竟是,索勃語課程的存在有損索勃人與德意志人間的情感交流,而且許多居住於索勃人與德意志人混居區的父母及社統黨區域黨部和政府官員反對學校提供索勃語課程,有鑒於上述因素,遂予前東德政府絕佳口實而起意廢除B型學校中的索勃語課程。至此可明確看出,前東德政府種種所謂提升索勃文化及其語言的措施不過是典型共黨極權政府的宣傳技倆,實則對內亟欲尋求國家社會一致化,基於此種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的指導原則,斷無可能坐視任何有礙國家社會一致性的事項發展,於是索勃語言政策的制定對前東德政府而言,充其量只是樣板文章,對索勃文化及語言的保障助益甚微。 在此尤須一提的是,相對於前東德政府對於索勃文化及語言的維繫措施流於形式 化,與索勃人同屬於西斯拉夫語系民族的捷克人及波蘭人則對於索勃人的語言及文化之維護及提昇反稍能略盡棉薄之力,例如在捷克成立的索勃中學(Sorbisches Gymnasium)是第一個為維護並復興索勃文化及語言而成立的中學,首度以索勃語發聲的廣播節目最初亦是在捷克開播。此外尚有許多有意繼續深造的索勃青年,大抵皆以捷克或波蘭做為第一選擇。在此明確道出,前東德社統黨政府根本並未真正關注索勃人的權益,所謂東德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澤披索勃人等誘人口號,終究不過是社統黨政府對外宣傳的技倆罷了。 (三) 兩德統一之後 兩德統一後,對於索勃民族的保護首見於西元1990年的「統一條約」(Einigungsvertrag)第35條的第14號議定書摘要,而有關語言部份則見第3條「索勃民族及其組織之成員得享有在公共領域各範圍內的保護,並擁有保存索勃語的自由」【22】,該條文即是針對勞席茨地區雙語政策的確保。另薩克森邦的西元1948年邦憲法中的「索勃人法」亦是統一條約中對索勃民族語言權益保障的法源之一。有關薩克森邦邦憲法中的索勃人法的兩條規定如下:「索勃人有權在索勃人居住的地方法院中使用索勃語,不受第184條【23】之規範」【24】;「索勃人有權使用索勃姓氏,索勃人可申請將原使用的德文姓氏改回索勃文姓氏,該申請一律依照姓名變更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25】。此外另須就索勃語在國家語言(Staatssprache)、法院用語(Gerichtssprache)、官方語言(Amtssprache)的地位以及在公共領域、大傳媒體與學校教育方面的使用情況進行析論。 1、國家語言 德國基本法中並未有任何針對國家語言的相關規定,由實際狀況觀之,德語為現 行唯一的國家語言。在此種情形下,德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當然不可能列入國家語言的層級。基本法已然如此,更遑論薩克森邦及勃蘭登堡邦兩邦憲法明載涉及索勃人聚居地勞席茨地區中索勃語在國家語言規定了。不過在薩克森邦中,索勃語在公共領域上的使用與德語具同等地位,例如選舉公告、通知及結果,皆以德語索勃語雙語並行之形式出現。 2、法院用語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84條明文規定:「法院用語為德語」,但如前所述,統一條 約中已然提到在索勃人的分佈區域,即在所謂的「家鄉縣市」(Heimatkreise)之法庭可以索勃語做為訴訟程序中的口頭及書面用語。但是曾經發生的真實情況卻是法官詢問皆為索勃人之相關兩造的原告與被告是否需以索勃語開庭,兩造都願意以母語進行訴訟,但法官的回答是,必需再擇日開庭,因法官本身不諳索勃語,故需要找到一位能操流利索勃語的法官才能使訴訟程序順利進行。 3、官方語言 德國行政程序法(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第23條第1款與社會法典(Sozialgesetz buch)第19條第1款及稅務法(Abgabenordnung)第87條第1款皆規定「官方語言為德語」。然而在行政程序法第23條第2款至第4款以及社會法典與稅務法同一條文又規定,對以外語進行行政程序的申請、請願或提案均可依例外原則處理。所以索勃人在行政機關中,不論是口頭或書面都可使用母語。但就書面方面而言,若承辦人員無法理解內容為何,則可要求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附上德語翻譯。行政機關在進行公告、通知時以德語為主、可以但無強制義務地,附上索勃語之翻譯。雖有這些規定,但真實情形為何?下索勃語電視節目「勞席茨」(Łužyca)的記者曾親身到卡門次及豪雅斯維爾達的城市行政機構實地進行測試,記者以索勃語詢問辦理汽車牌照等事宜,但櫃檯服務人員卻完全無法理解,乃以德語回詢:「您說的是索勃語嗎?」記者點頭。緊接著櫃檯服務人員表示將請一位會說索勃語的人員過來,但蹉跎良久,始來一位通曉索勃語的先生。他表示昔日從未有過索勃人要求以索勃語洽公的情形,係因每一個索勃人皆能使用流利德語之故。 4、公共領域 勞席茨可說是全德唯一在少數民族居住的領域中實施雙語的地區,包括交通標誌 、街道標示及方向指示、廣場名稱、橋樑名稱、公共建築物、郵局及火車站內的訊息告示,如站名或通行勞席茨地區的火車時刻表都是德語及索勃語雙語並行。雖為雙語標示,但德文字的規格顯然較索勃文大,當然標示牌上的文字大小以能清晰易讀為首要考量,不過卻不免遭受質疑,何以不是兩種文字大小完全相同地並列於標示牌上?此舉不啻使雙語標誌成為一種象徵性,並無實質意義(Pastor1997:177~180)。 5、大傳媒體 勞席茨地區以上索勃語發行的報章雜誌計有於西元1950年代創刊的「索勃新聞」 (Serbske Nowiny)、西元1990年創刊「新世紀」(Nowa Doba)、兒童雜誌「火焰」 (Plomjo)、天主教雙週刊「天主使者」(Katolski posol)、基督教月刊「你好!」(Pomhaj bóh);以下索勃語發行的則有週報「新報」(Nowy Casnik)及索勃文化雜誌「概觀」 (Rozhlad)。至於教育雜誌「索勃學校」(Serbska Šula)則是兼具上、下索勃語的刊物。 薩克森邦的中德電視暨廣播電台(Mitteldeutscher Rundfunk, MDR)自西元1992年起每週 播放19.5小時的上索勃語廣播節目,內容包括地區新聞、文化新聞、兒童新聞及體育新聞等。下索勃語的廣播節目則由勃蘭登堡邦東德電視暨廣播電台(Ostdeutsche Rundfunk Brandenburg,ORB)負責,每週播放6.5小時。電視節目則有東德電視台自西元1992年起播映每月半小時的下索勃語電視雜誌「勞席茨」(Łužyca)及中德電視台自西元1996年開播的雙週兒童節目「玩沙幼童」(Sandmännchen)。然而上索勃人希望除了中德電視台的「玩沙幼童」節目之外,在上勞席茨地區能有一個完全使用索勃語的電視節目。然中德電視台主管表示此舉有其技術層面上的困難,因為中德電視台頻道的播送範圍涉及薩克森邦、圖林根邦與薩克森-安哈特邦三邦,他們無法將電視節目分開播送,而且對於沒有索勃人居住的圖林根邦及薩克森-安哈特邦的觀眾而言,恐將無法接受一個完全播放索勃語的節目佔去中德電視台的時段。因此中德電視台主管表示,他們無法只顧及索勃觀眾的權益,遂使此議無疾而終。Tschernokoshewa(2000:61~62)分析此事件背後的意義是劃分文化的界線,以「不是-就是之模式」(Entweder-Oder-Modell)【26】來看待文化,亦即前述的「同質化」觀點:將不同文化及語言的民族或族群視為他者並排除在外(Exklusion nach außen)。 6、學校教育 中小學校教授索勃語的課程分為以索勃語為教學語言的A型班級(A-Klasse)及將索 勃語視為他種語言每週進行三小時課程的B型班級(B-Klasse)。但是索勃人今日面臨一項棘手的困境,由於經費短缺、出生率下降以及因為失業率過高而導致人口大量外移(Abwanderung)【27】,使得勞席茨地區人口總數因而持續下降,遂使勞席茨地區的許多學校被迫關閉,連帶導致索勃語的傳承更形困難。 另外為專司學齡前兒童索勃語教育之「歡迎語言中心」(WITAJ-Sprachzentrum)於 西元1998年3月1日成立「歡迎」幼稚園。該幼稚園的成立係依據西元1992年歐洲區域暨少數族群語言憲章 (Europäische Charta der Regional- und Minderheitensprachen)中所 言:「於私人領域及公開場合中使用區域及少數語言的權利為一不可剝奪之權利,這係與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致,而且符合歐洲理事會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保護公約之精神」【28】。「歡迎」幼稚園成立的宗旨是培養孩童具有索勃語及德語雙語能力-幼稚園中採「浸濡式」(immersion)教學,即完全以索勃語教學,學童在幼稚園中亦以索勃語交談。所以參加課程的孩童有可能是來自家中使用德語的索勃家庭或是德國家庭,他們在家說德語,在學校說索勃語。「歡迎」幼稚園堅信的原則是「一種語言-一個個人」(Eine Sprache - eine Person)(WITAJ-Sprachzentrum2002:10),因此如果從小在雙語的環境中成長,不僅有助孩童未來心胸開闊,對於其他文化有著較高的接受程度,而且有助於增進學習其他語言的能力,無形中亦培養出宏觀的世界觀。再者學會索勃語,等於是搭起東西歐的橋樑,因為同時擁有德語能力的背景,當能以索勃語為基礎對於未來進一步學習捷克語及波蘭語或是其他斯拉夫語言有極大之助益。 五、結論 「我們索勃人在德國的地位一向是很低的!」【29】。肇自西元10世紀「德人東向移民」運動開展以來,索勃人及其語言就始終難以擺脫德意志化的危機。經歷了千年持續不斷的外來同化壓力下,索勃語及文化的傳承幾近消失,時至今日,儘管索勃人仍為其母語及文化持續負隅抗拒德意志化的危機,然無可否認地,外人仍認為索勃語及文化已然是一個瀕臨「蓋棺」的文化。雖然外界對索勃語及文化的前景抱持著極為悲觀的看法,但對於索勃人而言,他們為自身語言及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而對抗德意志化威脅的奮戰已歷千年而不屈,他們絕不願坐視索勃民族自身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其血統相同的西斯拉夫鄰近諸部族般,無聲無息地步上德意志化的後塵。因此可想得見地索勃人這場為民族語言生存的戰役行將持續下去。 當然德國境內索勃人受歧視的際遇可說是與德國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且不論中世紀德人東向移民運動對索勃人的衝擊,時至近現代,隨著西元19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高漲及其後西元1871年德國的統一,使得索勃文化及其語言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而在此種德意志民族自信自滿的年代中,索勃人文化及其語言的存在猶若滄海之一粟,德人視之若非民族主義者欲將之儘速同化的態度,即是任其自生自滅,毫不在意。基於此種心態下,有關德國對於索勃人的語言政策當然也就乏善可陳,甚或動輒罷棄之。因此從西元1849年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憲法開始,直到德意志第三帝國納粹政權結束止,索勃語不是未受任何實質的保護與提昇措施,就是遭到全面禁絕打壓的地步。 前東德時代,基於宣揚社會主義優越性,社統黨政府遂極力強調該政權絕對有別於先前德國各時期政府對索勃語的打壓,並藉由一系列的樣板化措施,諸如勞席茨地區學校雙語教學、成立索勃文化機構及交通標誌雙語並列等措施來籠絡索勃人,藉由換取索勃人對政府交心,以支持前東德社統黨政權。此種心態不啻說明社統黨政府所關心者僅在於維繫己身政權的存在,根本無心於索勃語的維繫與提升,這使上述各類措施多數形同具文,幾無成效可言。兩德統一之後,索勃人提昇自身所屬語言與文化的希望再次浮現,但隨著聯邦國會否決少數民族條例,使得包括索勃人在內的德國少數民族期待獲得任何國家層次法律地位之保障的希望再度幻滅。 儘管索勃人在爭取維繫自身文化及語言權利的歷程屢受打擊,但他們猶仍奮鬥不懈,不斷藉由各種組織及活動以維繫與促進他們語言及文化的發展:「家園」是索勃民族的總樞紐組織【30】,下轄13個跨區域性組織,例如索勃學校協會(Der Sorbische Schulverein)、索勃藝術家聯盟(Der Sorbische Künstlerbund);另有家園出版社,專門出 版與索勃文化相關書籍及索勃語語言教材。在學術方面,除了索勃研究所專門研究索勃民族的語言、歷史及文化之外,尚有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的索勃學研究所 (Institut für Sorabistik),以索勃語文及文學為研究發展重點,亦設有索勃語教學師資 班。藝術方面,則有索勃民族劇團以戲劇與歌舞來呈現索勃文化的另一面。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傳統方式表達索勃民族音樂,另有以民間力量組成的索勃搖滾樂團,他們希望以年輕化的方式及輕快的搖滾音樂來發揚索勃文化及語言,藉此吸引年輕一輩的索勃人及青少年關注自身文化及語言,使之綿延不輟。索勃研究所並且每隔兩年舉辦學習索勃語言及文化的暑期學校,時至今夏(2002年)已達第八屆,參加成員源自世界各地,其中大部份為斯拉夫語系國家,索勃研究所此舉是希冀藉此將索勃文化向外傳播,儘可能讓世界其他地區的民眾知悉索勃民族及其文化,如此無形間或亦可收他人對索勃民族及語言維繫的關注之功。 索勃人積極推動發揚自身文化與語言的各類組織與活動的背後精神動力,不外乎是對自身民族及所屬文化與語言的強烈認同,因為他們無法坐視自己的語言與文化遭到「德意志化」而消逝的命運。藉由他們持續的奮鬥不懈,所以今日德東的薩克森邦及勃蘭登堡邦對索勃人分佈的勞席茨地區才能有著些許的保障索勃語的措施,誠然這些措施多數都僅是流於形式,實質功效不大,但必須強調的是,若無索勃人長期主動自發的為自身民族文化及語言的發展大力奔走,今日索勃文化及其語言恐將早已「蓋棺」。在此筆者不能不感慨,所謂自助人助,若無族群自身強烈自覺必須延續所屬文化及語言的永續發展,欲全然憑藉外界之力以扭轉語言流失之局終將勞而無功。今日即令德國政府對索勃人語言政策有意無意間的忽視,但索勃人卻絕不坐待德國政府態度的轉變,一切全依憑自身之力以維繫自身民族的文化及語言。反觀今日吾國臺灣族群的母語流失的情形已然極為嚴重,尤其是原住民語言及文化消失的危機更是迫在眉睫,面對昔日政府對原住民語言的未盡保護之責,今日政府當更有一番新思維,對於原住民語的保存應制定一套制度化的規範及具體措施,當然更重要的是族群本身自發性的力量,必須要使族群所屬成員都能充分認知到自身民族語言是祖先遺留下的珍貴財產,進而盡己所能地維繫自身母語的永續長存,如此自身母語方有續命之機。 附錄── 兩德統一條約第35條 1.茲此聲明為索勃民族及屬於索勃文化之自由。 2.確保索勃文化及索勃傳統之維護與持續發展。 3.索勃民族及其組織成員於公共事務範圍內,享有保護及保存索勃語之自由。 4.國家及各邦間基本管轄範圍及權限分配不受影響。 資料來源: Elle (1995):463-464 勃蘭登堡邦邦憲法第25條 索勃人(溫德人)之權利 1.確保、維持保存及促進索勃民族之民族認同及其原聚居區保護之權利。邦政府、鄉鎮及鄉鎮組織,應促進前揭權利之實踐,特別是有關保存索勃民族文化獨特性與確保索勃人之有效政治參與。 2.邦政府應致力於確保跨邦之文化自主權。 3.索勃人有權就公共事務中維護及促進索勃語言及文化,於中小學及幼稚園教授索勃語言及文化的相關知識。 4.索勃人有權於聚居區內,將索勃語標示於公共標誌上。索勃旗幟顏色為藍色、紅色、白色所組成。 5.索勃人之立法參與權。茲此確認在處理索勃人相關事務時,尤其是立法方面索勃人保有派員參加共同制定法令之權利。 資料來源: Elle (1995):464 薩克森邦邦邦憲法索勃人權利條文 第2條 Art.2 (4) 於索勃人聚居區內可共同懸掛薩克森邦邦旗、邦徽及索勃民族之旗幟與徽章。 第5條 Art.5 (1)德意志民族、索勃民族及其他民族公民皆為薩克森自由邦之公民。 (2)本邦確保及保護具德國公民身份之少數民族與少數族群之認同維護及其維護並確保對語言、宗教 、文化及傳承之保護權利。 (3)本邦尊重長期定居本邦之外籍少數族群之權益。 第6條 Art.6 (1)本邦內居住屬索勃民族之公民為享有平等權益之國民。本邦確保及保護對索勃民族之認同及其維護之權利,尤其是透過中小學、幼稚園及各項文化設施以保存及發展該民族語言、文化及傳承。 (2)於邦屬及地區性規劃中,應將索勃民族及其生活相關之需求納入考量,使索勃民族聚居區內兼具德意志及索勃文化之雙重特性得以保存。 (3)尤其在上勞席茨及下勞席茨地區索勃人跨邦合作屬於邦轄事務。 資料來源: Elle (1995):464-465 1994年7月7日公佈之勃蘭登堡邦索勃人權利組織法 (簡稱索勃人[溫德人]法) 第8條 語言 Art.8 Sprache 保護及促進索勃語,尤其是下索勃語。有使用索勃語之自由。Die sorbische Sprache, insbesondere das Niedersorbisch, ist zu schützen und zu fördern. Der Gebrauch der sorbischen Sprache ist frei. 第10條 教育 Art.10 Bildung (1)依父母意願,應給予索勃人(溫德人)聚居區孩童及青少年學習索勃語之機會。 (2)於索勃人(溫德人)聚居區之幼稚園及中小學內,以符合年齡的方式將索勃人(溫德人)的歷史與文化納入 遊戲設計及正規課程中。 (3)勃蘭登堡邦政府促進教授索勃語教師之養成、深造及進修。由本邦與薩克森自由邦共同合作。 (4)藉由成人進修教育促進索勃(溫德)語及文化之維護與保存。 (5)就經由聚居區之索勃(溫德)組織所推動成立,並以保護、促進及教授索勃(溫德)語言及文化且致力於達到雙語目標為首要任務之幼稚園及中小學,邦政府特別促進及支持。 第11條 聚居區之雙語標示 Art.11 Zweisprachige Beschriftung im angestammten Siedlungsgebiet (1)聚居區之公共建築、設施、 街道、巷弄、廣場、 橋樑及指示牌皆以德語及下索勃語雙語標示。 (2)就位於聚居區內具有公眾意義之建築物,勃蘭登堡邦致力於以德語及索勃語雙語標示。 資料來源:Pastor (1997):260-261 1991年7月3日公佈之薩克森自由邦學校法 第2條 德國人-索勃人混居區域學校 Art.2 Schulen im deutsch-sorbischen Gebiet (1)依其監護人意願,應給予在德國人-索勃人混居區全體孩童及青少年學習索勃語機會及針對固定科目及依年級進行索勃語教學。 (2)依據法律授權,文化部為處理針對德國人-索勃人混居地區索勃中小學或其他中小學制定必要的特別法令規定,尤其是關於 1.組織 der Organisation; (3) 此外薩克森自由邦內所有中小學應教授有關索勃人之歷史與文化的基礎知識 。 資料來源:Pastor (1997):275 1991年5月30日國民協定關於中德電視暨廣播電台(MDR)之條文 第6條 Art.6 (3) 中德電視暨廣播電台製作節目時,應將人民團體,包括少數族群或民族之權益納入考慮。 資料來源:Pastor (1997):290 1991年6月27日公佈之薩克森邦私人電視暨廣播電台及新成立媒體事業法規(薩克森邦私人廣電法) 第27條 法律形式及組織 Art.27 Rechtsform und Organe (1) 依據本法所訂之任務由邦屬機構執行,該機構具公法人資格且其址設德勒斯登。 (2) 此邦屬機構為獨立且具自治權性質,但不具宣告破產能力。 (3) 邦屬機構組織由以下組成 1.代表大會 die Versammlung 2.行政委員會 der Verwaltungsrat 3.主管 der Direktor 第29條 代表大會之組成 Art.29 Zusammensetzung der Versammlung (1)共28名成員 16. 索勃人組織代表一名 資料來源:Pastor (1997):290 1991年11月6日公佈之勃蘭登堡邦東德電視暨廣播電台法 第4條 節目製作委託 Art.4 Programmauftrag (3)製作節目時應將勃蘭登堡邦之區域性節目、文化多樣、與索勃文化及語言納入節目範圍內。 第16條 人員組織、任期、費用返還 Art.16 Zusammensetzung, Amtsdauer, Kostenerstattung (2) 委員會20 個成員由以下機構及社會團體組成 14. 索勃組織代表一名 資料來源:Pastor (1997):290-291 參考文獻
Schreiber, Hermann. 1984. Die Duetschen und der Osten. Toivanen, Reetta. 2001.Minderheitenrechte als Identitätsressource? Die Sorben in Deutschland und die Saamen in Finnland.(Dissertation,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Münster: LIT. Tschernokoshewa, Elka (Hrsg.).1994.So langsam wirds Zeit. Kulturelle Perspektives der Sorben in Deutschalnd. Bonn: ARCult. Tschernokoshewa, Elka. 2000.Das Reine und das Vermischte. Die deutschsprachige Presse über Andere und Anderssein am Beispiel der Sorben. Münster: Waxmann. Urban, Rudolf.1980.Die Sorbische Volksgruppe in der Lausitz. 1949-1977. Ein dokumentarischer Bericht. Marburg: Johann-Gottfried-Herder-Institut. WITAJ-Sprachzentrum.2002.WITAJ. Informationen zur zweisprachigen Erziehung. Bautzen: WITAJ-Sprachzentrum. 注釋 【1】民族語言的功能在於凝聚民族意識及促進民族認同,但基本上這是人為建構的,是後來才被創造出的。民族語言的真正內涵在於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言之中,精煉出一套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後再把所有的同行語言降格為方言。在這種建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應該選那一種方言做為民族標準語言的基礎。從歐洲語言的發展史看來,每一支歐系語言都是奠基在這種地區性的基礎上。(霍布斯邦 1997: 72-73) 。 【2】原文為Deutscher im Sinne dieses Grundgesetzes ist vorbehaltlich anderweitiger gesetzlicher Regelung, wer di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besitzt oder als Flüchtling oder Vertriebener deutscher Volkszugehörigkeit oder als dessen Ehegatte oder Abkömmling in dem Gebieb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nach dem Stande vom 31. Dezember 1937 Aufnahme gefunden hat. 【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被迫遷離東歐與奧德河(Die Oder)及其支流奈瑟河(Die Neiße)以東的原德國 東部領土(東普魯士(Ostpreußen)、西利西亞(Schlesien)、東勃蘭登堡(Ostbrandenburg)及波曼恩(Pommern))的德意志民族,總數高達一千五百萬人之譜,這些被逐出原德國東部及東歐家園的德意志人是自中世紀中期「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Die deutsche Ostsiedlung)運動開展以來,即從德意志西部逐步遷居至德國東疆 及東歐,並落籍於當地的德裔後代,他們世居當地皆已歷數百年,甚至千年之久。這些中世紀中期以來陸續移向德國東疆及東歐的大規模德人東移行動,被當代德國史家稱為「德人東向移民運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第三帝國為了在東歐擴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因而揮軍東向,兵鋒所及,包括俄羅斯半壁江山在內的東歐盡數納入納粹鐵蹄之下,亦使東歐斯拉夫諸國慘遭兵燹之禍及納粹德軍之迫害。緣自此種仇德情結使然,因此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歐各國遂大舉驅離世居境內的德意志人,而此項驅逐行動復因「波茨坦宣言」(Potsdamer Deklarationen, 1945)的保障而成為合法之舉。根據 波茨坦宣言之相關規定,戰前居住於原德國東部及東歐各地的德意志人必須於戰後盡數遷往德國及奧地利,於是高達一千五百萬的德意志人遂因而橫遭逐離家園之禍。這場「人造」的民族遷徙行動,其規模之大,甚且遠遠逾越西元四至五世紀間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DieVölkerwand-erung or The Movement of Peoples)。然而此項人為強制措施實係一場人間悲劇,絡繹不絕的德人難民潮在其西遷之途上,飽受東歐各國軍民侵奪劫掠、流離顛沛之苦,總計命喪西遷德國及奧國之路者,超過兩百萬人以上。然而這項驅離行動未盡徹底,許多東歐德意志人透過行賄手段及隱藏其德裔身份而持續居留於當地,估計今日仍約有兩佰萬德意志民族散居於東歐、中亞及亞俄各地。有關德意志民族移入原德國東部及東歐各地與二次大戰後的被逐歷程,請參閱杜子信 (1998)。 【4】分別為薩克森邦(Sachsen)、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圖林根邦(Thüringen)、梅克倫堡-前波曼恩邦(Mecklenburg-Vorpommern) 及勃蘭登堡邦(Brandenburg)。德國國內以「 新邦」 (neue Bundesländer)稱呼前東德五邦。(筆者按:波曼恩在戰前原為德國之一邦,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國將奧德河及其支流奈瑟河以東的前德國東部領土劃歸波蘭,於是波曼恩遂被從中切斷成兩部,分別為位於前東德的前波曼恩及位於波蘭的後波曼恩 Hinterpommern,兩者間以奧德河為界。) 【5】弗利斯蘭人為為分散三地的少數民族,其血統係屬西日耳曼人種,語言亦屬西日耳曼語之一支,因此該民族實與德意志人及尼德蘭人(荷蘭人)血緣相近,但因該族群的文化及語言保有更原始古老的型式與風貌,因此該族群自認為是分布在德意志及尼德蘭境內的一支少數民族。該族群人數最多的是分布在尼德蘭聯合王國(荷蘭)弗利斯蘭省的西弗利斯蘭人,近五十萬人仍操西弗利斯蘭語,並為該地區的第二官方語言。其次尚有約三十五萬的東弗利斯蘭人定居於德國的下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但所使用的語言為低地德語,至於東弗利斯蘭語只通行於該邦的薩特蘭地區(Saterland),今日當地仍操東弗利斯蘭語的弗利斯蘭人僅存一千五百人左右。另外分布在德國北部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操北弗利斯蘭語的北弗利斯蘭人,則是三支弗利斯蘭人中人數最少的,近一萬人。今日弗利斯蘭語被歸列為歐洲少數語言之一。(POGROM 1994:14) 【6】原文為 Die Erziehungsberechtigten entscheiden, ob ihre Kinder die Schule einer nationalen Minderheit besuchen sollen。 【7】據1994年統計,德國超過二十萬以上的外來移民分別是土耳其1,918,395人 、前南斯拉夫各國929,647人 、義大利563,009人、希臘 351,976人、波蘭 260,514人 (Schmalz-Jacobsen und Hansen 1995: 555-557) 。 【8】依據Howard(1995)的觀察,德語為德國東西部的共同語言,純由語言學的角度而論,東西部唯一的差異僅是各地的地區性方言之不同。在宗教上,德東人民較多信仰基督教路德教派或是無神論者。但這兩點並非是構成德東人民認同的主要因素(Howard 1995:130 注釋28)。 不過若以文化差異的層面觀之, Stenger(1997)認為,雖然德東及德西人民所操語言皆為德語,但是他們卻是兩個不同的溝通團體(Komm-unikationsgemeinschaft) ,此處所指涉的並非僅是表面上的辭彙使用區別,而是受到長久以來的生活環境 相關的結構影響之深層的語意差異(semantische Unterschiede) 。德東及德西民眾原本因生活於相異社會所 產生的陌生感並不因兩德的統一而減少,反倒有增加的趨向。因為原本兩德人民所期待的是隨著國家統一之後能創造出文化共同性(kulturelle Gemeinsamkeit),而建構共同文化性的希望之所繫即相同的語言。 然而當德國真正統一之後,取而代之的卻是集體失望的歷程(Stenger 1997:181-182)。 【9】這是Max Weber對族群所提出的核心定義之一,他認為族群本身與其他族群不同的文化及風俗習慣, 會使族群產生榮耀感及尊嚴。 【10】德國東西部間思維及行為差異,就某種程度而言亦是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德國易北河(Die Elbe)以東之 地是「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以後所拓展的新領域,當時斯地充斥著封建領主所掌控的大莊園,這些封建領主係由一個貴族地主階級所構成,即「青年領主」(Jungherr)階級,其後這個德文字音轉為「容克」(Junker)。容克階級的形成對於德國東部有著極大的影響,他們憑藉著掌控大批莊園領地的基礎而發展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其後並進一步晉身仕途及投身軍旅,對於其後的普魯士王國,乃至德意志第二帝國都具有強大的政經社影嚮力。然無可否認地,容克階級的崛興與壯大基本上是建立在對莊園農民無情的壓迫及剝削上,長此以往,易北河以東之地,終而漸漸形成了容克專制保守的色彩,這與德境西部萊茵河地區所蘊育出的自由寬容精神是截然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容克階級雖被徹底摧毀,但緊接著東西德的分裂,東德復又淪入共黨之統治,表面上共產黨人的意識型態與容克階級是處於極端對立的兩極,然實質上專制保守的心態則無甚差異。兩德雖於西元1990年10月3日統一,然長期歷史發展上的差異,使德東人民仍保有濃厚的保守反動心態,再加上德東經濟始終為德國政府及德西民眾的沉重負擔,以致於今日德西民眾對德東人民不免心生反感而蔑稱其為「東部佬」(Ossi)。 【11】原文為 Wenn die Deutschen lernten, in ihrer Größe mit uns, den wenigen, von gleich zu gleich zu leben – welch ein neues Bild von Deutschland sähe die Welt ! 【12】當代著名索勃作家,除了以索勃文及德文寫作之外,尚致力於索勃文與其他斯拉夫語系及與德文的翻譯工作。 【13】溫德人稱謂的來源,可能性有三:第一種可能性是西元一世紀時羅馬史家稱呼當時居住於喀爾巴仟山(Karpaten or Carpathian Mts.)以北的斯拉夫部族為Venedi,其後始音轉為溫德(Wenden);第二種可能性是指其為「金髮者」,可能為該民族成員多為金髮有關;第三種說法則意謂「皈依者」,隱含有貶抑的色彩,係因德人在數世紀的東向移民及擴張運動後,已然完全將溫德人征服,並將之德意志化及基督教化。另有一種說法則指稱溫德人係日耳曼民族汪達爾人(Vandalen)移向南歐及北非後留在中歐的殘餘部族,後來受到斯拉夫人向西遷徙,才被西斯拉夫民族所同化並轉操斯拉夫語,而其族名亦由Vandalen音轉為Wenden;此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觀點尤為納粹黨人所倡導。然今日史學界及人類學家已然證明兩者間毫無關聯,上古中古之交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係舉族遷徙,因此汪達爾人並未在其遷徙之途上遺留任何部落。詳請參閱Charles Higounet (1986): 28.; Karlheinz Blaschke(1997):10。 【14】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運動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所進行的疆域開發及移民運動之一環,其歷程延續千年之久,由西元8世紀一直延伸至19世紀初,其間共分三波東移大浪潮:分別為西元8~11世紀、12~14世紀及17~19世紀。在此漫長的歲月中,大批德意志民族受生機所迫而移向德國東部及東歐地區,其間歷程大半是以和平方式進行,時或亦有武力征伐之舉。在西元19世紀中葉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中,此一史實淪為意識型態鬥爭的工具,德意志及斯拉夫史家不約而同地將此一史實視為「德人向東壓進」(Der deutsche Drang nach Osten`),一方歌頌為英勇的德意志民族東進之先鋒,另一方則醜砥為惡魔般之千年 德人東侵惡行。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的意識形態化對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的中東歐政局影響深遠,20世紀德意志第二帝國及第三帝國的兩度揮軍東進,某種程度上即是受到德人東向移民史實被意識形態化的結果。有關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運動的始末及其意識型態化,請參閱杜子信(1998)。 【15】Melange 為奧地利咖啡,咖啡與鮮奶油及牛奶各佔一半,因此引申為「混合物」之意, Melange-Effekt的概念由Jan Nederreen Pieterse (1998)所提出。 【16】始於西元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近代民族主義出現以後的核心概念,因為基於民族主義而型塑國家的歷程中所強調的即是在民族內部從相同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傳統等建立集體認同,以對外有別於與他們不同的「他者」。 【17】就借字來說,在索勃人原來的傳統生活範圍內的借字比例較低,例如自然、動植物及農業方面分別是3.6%、12.3%、13.8%;而若非屬傳統範圍內則較高,如職業或社會面向達27% ,與服飾相關的字彙則達34.9%(Brijnen 1992:14)。 【18】語出 DOMA. Fotographien aus der Lausitz. Bautzen : Domowina 1995 . S.128。原文為 Die machtsituation in Deutschland ändert sich, an der lage der wendisch-sorbischen sprache ändert sich nichts. Sie nimmt ab.(筆者按:本句中的machtsituation 、lage及 sprache為名詞,依德文文法名詞的第一個字母應為大寫,但當代索勃詩人Domašcyna皆採索勃文文法而將首位字母改成小寫,筆者猜測她欲將索勃文與德文結合,以做為她身處兩種文化與兩種語言之間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19】原文為 Den nicht deutsch redenden Volksstämmen Deutschlands ist ihre volkstümliche Entwicklung gewährleistet, namentlich die Gleichberechtigung ihrer Sprachen, soweit deren Gebiete reichen, in dem Kirchenwesen, dem Unterrichte, der inneren Verwaltung und Rechtspflege. 【20】原文為 Die fremdsprachigen Volksteile des Reichs dürfen in ihrer freien volkstümlichen Entwicklung, besonders nicht im Gebrauch ihrer Muttersprache beim Unterricht sowie der inneren Verwaltung und Rechtspflege beeinträchtigt werden. 【21】原文為 Die fremdsprachigen Volksteile der Republik sind durch Gesetzgebung und Verwaltung und in ihrer freien und volkstümlichen Entwicklung zu fördern; sie dürfen insbesondere im Gebrauch ihrer Muttersprache im Unterricht, in der inneren Verwaltung und in der Rechtspflege nicht gehindert werden. 【22】原文為 Angehörige des sorbischen Volkes und ihre Organisationen haben die Freiheit zur Pflege und zur Bewahrung der sorbischen Sprache im öffentlichen Leben. 【23】法院組織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第184條明文規定「法院用語為德語」(Die Gerichtssprache ist deutsch)。 【24】原文為 Das Recht der Sorben, in den Heimatkreisen der sorbischen Bevölkerung vor Gericht sorbisch zu sprechen , wird durch §184 nicht berührt. 【25】原文為 Die Sorben haben das Recht, ihren Vor- und Zunamen in sorbischer Schreibweise zu führen. Angehörige der sorbischen Bevölkerung können einen Antrag auf Änderung ihres deutschen in einen sorbischen Namen stellen, sofern ihr Name germanisiert worden ist. Dem Antrag is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 über Namensänderungen stattzugeben. 【26】相對的,若以「不是-以及-就是之模式」(Entweder-und-Oder-Modell)來觀察文化,那麼我們將可看到文化的多樣性,而所謂的 「差異」(Differenz)反而提供的是另一種觀察人類生活的角度,且在此模式的詮釋之下,文化是生動的(dynamisch)、在歸屬(Zugehörigkeit)與區別(Trennung)之間持續地交替著(參閱Tschernokoshewa 2000:115-122)。 【27】失業率過高(約20%),並非完全僅是索勃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德東地區的難題,因此大量人口移往德西以尋求工作機會。 【28】原文為 Das Recht, im privaten Bereich und im öffentlichen Leben eine Regional- oder Minderheitensprache zu gebrauchen, stellt ein unveräußerliches Recht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im internationalen Pakt der Vereinten Nationen über bürgerliche und politische Rechte enthaltenen Grundsätzen dar und entspricht dem Geist der Konvention des Europarats zum Schutze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29】西元2002年7月31日筆者與位於包岑的索勃研究所(Sorbisches Institut)研究員Ludwig Elle博士(本身為索勃人)談話時,他對索勃人在德國的處境所發表的看法。 【30】該組織自西元1912年成立之後,一直扮演著促進索勃人權益的重心組織,但在前東德社統黨專政時期,「家園」組織被社統黨政府當成意識形態的工具,使之無法真正彰顯它原有的功能。故在兩德統一之後,「家園」組織開始在人事及結構上進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