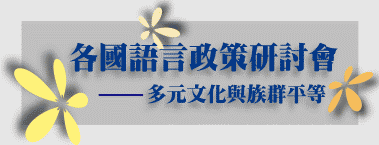
|
|
|
比利時語族文化共同體與行政自治區之演變與現況 廖立文 Xavier Liao◎Independent Researcher, Brussels, Belgium |
|
|
一、前言 同一領土上的兩個或是多個語族間之所以有經常性的摩擦與衝突,原因不單在語族彼此使用的語言不同而已,還有語言背後所隱藏的文化習性、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型態的根本差距, 造成相互間在公共事務的認知與處理方式上的差距。另外,「語言不只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它還有相當的政治關聯性。也就是說,不單是語言的使用決定了政治權力的分配,同時,語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施正鋒,1998:60) 比利時的法蘭德斯語 (荷語) 族群在自1830年比利時獨立建國起,即長期受到不及國內總人口半數的法語族群壓抑。該國法語人則憑藉著既得政治勢力和其語言優越感,宰制國內語言族群的共存事務,導致多數人口的荷語族群反成弱勢。這個例子不論從語言學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都是相當值得探討的研究個案。 比利時的荷、法兩大語族歷經時代變遷,各族群的經濟實力彼此消長,國內的族群政治版圖有所重整。加上荷語族人多年的積極運動爭取, 荷語族人終於得到應得的基本權利。不過兩大語言族群的衝突情況,至今依然存在。不僅如此,歐洲聯盟建立後,對各國族群問題的介入,以及比利時本身境內存在愈來愈嚴重的移民問題, 使得比利時原本複雜的語族衝突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法籍學者高格孚(Corcuff,2002,xi)曾將台灣喻為「國家認同問題的試驗場」(Taiwan,A laboratory of Identities)。無獨有偶,比利時學者薇特(Els Witte)和梵費爾特霍文(Harry Van Velthoven) 則將比利時視作世界唯一的雙(多【2】)語主義、語言社會學與語族權力傾軋的試煉場。要了解與解決存在於同一國家領土中之不同語族間的共存問題, 須探尋過去的歷史,分析現有面對的問題,再比較世上其他類似的國家或區域的經驗,以便找出多種可行的解決方案,透過實際執行來獲取實驗成果,達到目的。這份報告盼以簡明但扼要地方式,展陳比利時在語言文化共同體與語族自治區的發展過程與遭遇問題,期待能提供給國內學者與相關行政單位作為未來規劃台灣國內協調語族共存並保障其各自文化事務的參考。 二、比利時簡史 比利時王國號稱歐洲,或更精確地說是西歐的「心臟」的。但它其實不過只是剛從1830年才正式宣告獨立的年輕君主立憲國家,現有土地面積約32,000平方公里,與英國隔英吉利海峽相望,國土的北、東、南分別與荷蘭、德國、盧森堡與法國接壤。人口約有一千二百萬,法、荷人口的比例約為4 :6。目前比利時所在的區域曾在歷史上先由塞爾堤克人(Celtic)占居。公元前五十七年,羅馬人將塞爾堤克人驅逐, 佔領該地區直到公元五世紀左右。其後法國人的祖先法蘭克人(Franks) 取代羅馬人,並 將基督教文明帶入當時所謂的「低地國」(The Low Countries),即現今比利時、荷蘭一帶。 在法蘭克國王科羅威(Clovis)移都巴黎之前,一度以現比利時南部的城市都爾內(Tournai)作為王城。十世紀時,歐洲境內貨物運輸開始沿著河流作為交通路線發展基點,許多聚落沿著河岸或河流轉折的口袋形區域興起。這些聚落透過地理優勢,逐漸吸引許多居民聚集, 從事配合貨運交通需求的週邊服務行業。許多大型城市自此奠定日後的規模基礎。這些城市不僅因通商貨運之故, 不僅在城市規模與財富均迅速發展。更藉地利與資訊暢通之便,發展各自的貿易產業。位居現今比利時北部的法蘭德斯地區 (Flanders) 正是當時以上述原因發展城市與貿易產業的典型區域。當時該地區以優質的紡織產品聞名歐洲。而現今比利時南部的瓦隆尼區 (Wallonia) 也是當時歐洲金屬冶鍊工業的重鎮。十三世紀後,歐洲商業自陸路與內陸河運轉往海運發展,法蘭德斯臨海的布魯格(Brugge)曾居北歐港市聯盟之首。日後因海港漸漸淤塞,該港市地位最後由法蘭德斯北方的安特衛普港取代。 從十五世紀末到十八世紀末的三個世紀間,比利時一度成為歐洲幾個宗教信仰不同強權的殺戮戰場。遠從地中海信仰基督教(羅馬公教/天主教)的西班牙與北方信奉新教的荷蘭,東邊的奧地利與南方接壤的法國都曾經為了伸張己身權力在比利時的土地進出。這個不穩定的國際局面直到1794年拿破崙以軍事手段將現在的南尼德蘭(the Southern Netherlands)及比利時列日(Liege)地區納入法蘭西帝國版圖, 比利時邁入獨立建國前的法屬時期。 當時雄霸歐洲一時的拿破崙,在1814年的滑鐵盧(Waterloo) 一役敗給英國、荷蘭、普魯士與奧地利的聯軍。於是比利時地區的統治權便從法蘭西帝國轉到荷蘭。 滑鐵盧戰後,歐洲各國在奧地利首都召開著名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重新分割由拿破崙東征西討佔據的各國領土。會中決定把北尼德蘭 (the Northern Netherlands) 與南尼德蘭(現法蘭德斯)及列日王子國(現瓦隆尼)交歸荷蘭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所屬,以圍堵法國日後可能在北方的擴張行動。信奉新教的威廉一世在當時屬地境內極力主張工業,並在法蘭德斯區內強行推動荷語,曾遭新屬地以法語為時尚語言的荷語區上流社會人士極力反對。另外,在威廉一世強力推動工業化的政策下,佔當時法蘭德斯區人口多數的農村居民備感競爭壓力,天主教會便藉支持農民為由,聯合資本家與具備自由主義思想的中產階級反對信奉新教的荷王。1820年代末,布魯塞爾發生多起暴動事件,威廉一世派兵鎮壓,受到南尼德蘭居民極力反抗,終於1830年九月正式撤軍。由資本家與人民代表組成的臨時政府宣佈比利時正式獨立,並於次月召開國會制定憲法。 早自工業革命以來,英國一直企圖在歐陸建立一個外交與商業的橋頭堡。由於距離之便,英國與當時南尼德蘭地區工業來往早已相當頻繁。比利時宣告獨立後,英國即以聯盟國身分在倫敦召開國際外交會議,向歐洲各國尤其荷蘭施加壓力,共同正式承認比利時脫離北尼德蘭(荷蘭)而獨立。並認可其第一任國王李奧波一世(Leopold I)的國家法定代表人地位,比利時正式成為國際認可的新國家。就國際政治角度而言,比利時取得明確的合法地位。然而這對比利時國內語言族群衝突的發展,其實才是序幕的展開。 三、比利時荷語族群追求認同發展過程 1. 1830年獨立建國以前 比利時之所以有複雜的語族問題,主要源自十八世紀拿破崙帝國的併吞比利時。拿破崙的軍隊擊退英荷聯軍後,將現今比利時北部的南尼德蘭地區劃進了法國的版圖。法國統治比利時的廿年間(1795-1814),為求帝國的統一,將法語規定為新屬地的法定語言,強制新屬地的政府機構及法庭等機構隨即以法文為公文語言,並開始在學校實施法語教育。當時以採煤與煉鐵工業為主的比利時南部列日(瓦隆尼)地區居民,原本就以法語系的方言為其生活語言,並未受到太多衝擊。而北方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南尼德蘭地區(包括布魯塞爾)的居民原使用屬於日爾曼語系,總稱為法蘭德斯語的各種方言為主。這個語言以荷文為主幹,仍沿用相當多拉丁和希臘古語,但尚未到達成熟語言的程度。此外,南尼德蘭區當時仍以農村為其主要社會結構單位,除了城市之外,鄉村地區的村落間缺乏(不需)交流,導致各地方言各自封閉發展,差異甚鉅【2】。總之,當時的法蘭德斯並沒有通用的標準法蘭德斯語。 基於法國在歐洲歷史上的長期強勢, 法文已是當時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外交語言。再者,法蘭西民族自久以來對於文化藝術的注重,使得由非法語系國家向來以法語為上層社會的通用語言。在這種價值意識型態下,拿破崙的佔領其實受到比利時南北兩部不同態度的肯定:首先對原先就以法語方言為主的地區,應說是回歸母語人的統治,人人喜悅倒不至於,至少沒有太大的反感;對於南尼德蘭地區來說,因為政治權力的更迭,導致語言政策的改變,對於中下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除了與官方的接觸需透過翻譯辦理,帶來不便外,沒有更惡劣的影響。反之,對城市中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已有既得利益的貴族與實業家,或是才拜工業革命之賜,逐漸擠身上層社會的「中產階級」【3】而言,法蘭西帝國的佔領不但對其利益沒有任何影響,反倒為其在上層社會使用法語製造了完美的藉口,以便突顯其有別於中下工農階級的社會優越地位。 1814年拿破崙戰敗給歐洲聯軍後,被迫將南尼德蘭和列日地區交給荷蘭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並且將邊界退回現今北法的加萊(Calais)。威廉一世將南尼德蘭納入版圖後,跟拿破崙一樣,先要統一新屬地的行政語言,於是頒令規定法院及行政體系全面改用荷文。在南尼德蘭法蘭德斯方言區,必須完全使用荷語。在南部的列日(法語地區), 先訓練公務人員與法官使用荷語之外, 並開始在中等學校實施雙語教學,限定固定時數的法語與荷語雙語教學,讓學生開始學習荷語。依照學者薇特(Els Witte)和梵費爾特霍文(Harry Van Velthoven)的說法,這算是比利時史上首度的雙語主義起源。 從原則與實施方式來看,威廉一世的語言政策與拿破崙當初兼併比利時所實行的語言政策相比,其實是較具包容性,且較沒有極端的排他性。可是實地實施的結果確南轅北轍。不僅在執行過程當中相當不順,最後還導致比利時上層社會與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抗,使得荷蘭不得不退出這塊土地,任比利時獨立建國。 研究分析威廉一世語言政策失敗的原因,其實與政策本身並無太大的關聯。最重要的因素還是當時存在於南尼德蘭區上層社會中的社會階級意識型態所致:當時的法語區居民與地方政府對荷蘭的統治心生抗拒,在所難免。但是威廉一世在該區執行語言政策時採取懷柔的漸進模式,意圖逐漸化解反抗的敵意,結果並沒有預期地那麼糟。 出人意料的是,主要的反對聲音居然是來自原本就在民間普遍使用法蘭德斯語(荷語)的南尼德蘭地區。南尼德蘭區上層社會自拿破崙佔領前,便已將使用法語轉成製造社會階級優越感的一種工具,更是既得利益群體的共同識別標誌。拿破崙佔領該區時,法語更加成為區別社會階層的參考指標。當威廉一世在正式佔領南尼德蘭後第四年(1819年),於南尼德蘭四個省份強制官方機構與法庭使用荷語時,發現居然沒有公務員能以荷語工作。 箇中原因除了因為在法蘭西帝國統治下,法語的使用與教育已有將近一世代的時間。上層社會自然早已習慣並且希望保有這份社會優勢地位。連從小接受法語教育,即將進入體系中堅地位的新一代,除了對要學一種新語言大起反感外,更不願才剛到手的社會階級優勢。當然,還有自久以來的社會階級意識型態作祟:上層社會人士多半持有「語言沙文主義」(linguistic chauvinism)【4】的態度, 無人願意使用其所謂「農民的」或是「鄉下人的」粗鄙語言,因此心理排斥與抗拒感自然更大,造成改用荷語的動機低落。 1828-1829年比利時公務人員與上層社會人士提出請願書,要求威廉一世同意荷語區的法語使用者可以保有在公文書,軍隊和法律業務方面使用法語的權利; 法語區則可以完全以法語為官方語言。這份請願書等於一份宣戰書,當然引發了強烈的反應。當時的比利時天主教會也反對信奉新教的荷蘭國王統治比利時,因此鼓動農村地區居民配合城市的自由派人士群起暴動,在幾個大城市接連發生革命事件。威廉一世派兵鎮壓未果,最後撤兵。比利時全國推派各區域代表,成立臨時議會,組織臨時政府,宣告獨立。 2. 1830年獨立建國以後 由於主導革命與獨立建國的主要成員是法語人和親法語的荷語區上層社會人士與中產階級,1830 年比利時獨立建國後,按照憲法精神所採取的議會制的多數決原則,荷語的合法性被「民主地」排除在議會殿堂之外。非但如此,儘管比利時境內荷語人口多於法語人口,但是當時掌握重要社會資源如公務人員、軍隊、企業等都是親法語者,正如薇特(Els Witte)和梵費爾特霍文(Harry Van Velthoven)所言:
眾多為了追求更多生存機會的荷語人,只得捨棄使用母語的天賦權利, 屈於現實學習法語,變成雙語使用者。這個現象尤其出現在工業化與商業化較明顯的城市地區,如布魯塞爾(Brussel)、根特(Gent)、安特衛普(Antwerpen)等。為了反對這種不公,以農民為主的法蘭德斯西部,一則距離首都最遠,另者也是最受到所謂上層社會歧視,便有「法蘭德斯運動」(Flemish Movement)的興起,為荷語追求跟法語一般的法定語言地位。 建國後的第一個卅年間, 「法蘭德斯運動」一方面在法語族群(含荷語區的親法語人)的政治與經濟強勢下,無法抬頭。另外運動主導者的平均素質因為教育程度尚未抵達一定程度, 受到議會政治的門檻條件限制, 在數量與品質方面均無法達到邁進議會殿堂內追求應得權利的地步。更因為運動的支持者多在農村或偏遠地帶,經常被抹黑為鄉村的農民運動,或是被自由派的反宗教人士稱作教會在其信徒眾多的區域所主使策動的政治干預活動。 「語言既然反應的是政治現象,則語言問題必須使用政治方式來解決。」(施正鋒,1998:60)在比利時獨立建國一個世代以後, 具有法蘭德斯精神的新生代多半在法語壟斷的政經社會中受有良好教育,足以代表母語同胞參加選舉,進入議會以民主方式為同胞爭取應得權利。「避談語言問題,只能延緩現有的政治不平等。」(施正鋒,1998:60)之後便有愈來愈多涉及語言使用的法律在議會中通過。其中重要的有1873年通過:在法蘭德斯(包括布魯塞爾)所發生的法律訴訟中,若確定被告為法語母語使用者,訴訟中必須以荷語進行, 以避免司法體系袒護法語(既得利益)被告,影響荷語原告權益。1878年准許在政府機構當中使用荷語。1888年高等教育中可使用荷語教學。最後終在1898年所訂定的「平等條款」中正式將荷語和法語定於在相同的法定地位。 儘管荷語終在十九世紀末經由「法蘭德斯運動」的推動下,成為法定語言。但是兩大語族間的摩擦與觀念差距,仍然在許多公眾事務議題上爭執不下。時間延續到兩次大戰間,比利時均受到德國的佔領。第一次大戰,德國運用兩大族群差別待遇, 以加深族群間的仇隙,製造佔領區兩大語族的相互牽制。 曾強將法蘭德斯人推上比利時西南部戰場,抵抗法國軍隊。二戰期間,德軍自荷蘭與比利時東部列日地區進攻,遭到荷蘭與比利時法語人的強烈反擊。比利時當時國王李奧波三世(Leopold III)眼見德軍在荷蘭的強勢攻擊,以及荷蘭強烈反抗後的慘狀,為求比利時居民安全,同意不戰而降。這也讓比利時境內以法語區為主的抗德行動轉為地下。比利時被佔領後,德國佔領區政府利用荷語人在文化與行為意識均與日爾曼語族的德國人接近,或多或少在佔領心態上對荷語人較友善溫和。另一方面,法語區內地下抗德事件不斷, 德軍佔領政府於是重施一戰時期故技,刻意對兩大語族的控制採用差別待遇模式, 以之間的隔閡來打擊地下抗德分子的活動。便有法語區的抗德份子與荷語區的社會主義及共黨份子為主的抗德份子結合結果,並從此將法蘭德斯視為意識型態上的通敵者(collaborators),仇視甚烈。 二戰結束,德國自比利時撤軍。德國人走了,輪到比利時自己開始進行所謂戰後的「肅奸報復行動」(La Repression,1945-1950)。各地被認為在戰時與德國人從事各種型式合作的通敵者,全數遭到逮捕。有的遭到就地槍決; 被逮捕送到法庭的,也在沒有辯方律師的出席之下,在罪證未經證實便即定罪,判以死刑、長期囚禁或放逐國外,被列入所謂黑名單,終身不得再回返國土一步。 所謂「通敵者」(collaborators) 的定義:可廣義地說,是指戰時與德國軍隊合作的比國官員與軍民。上從戰時與德軍妥協,出任佔領區人民自治政府的官員,下至曾藉著跟德軍官兵密切往來,以換取較多生活物資的年輕寡婦。而其中最令人戰後比利時人民憎惡不齒的,自然是那些曾密報比利時地下反抗軍行動給德軍的賣國賊。不過,在這些通敵案當中,不乏有人因細故得罪他人,因此遭誣告通敵,至死不知究竟何時犯下通敵罪行的冤案。更不乏左派與共黨份子在戰後控制政權,利用肅奸報復行動來打壓右派保守勢力,消滅異己。這個「肅奸報復行動」的仇恨,至今尚未化解。當時存活的「通敵者」,至今還因有案在身,不僅自己,連帶家人的公民權遭法律褫奪、基本社會福利權被削減。至於究竟誰是忠是奸的真相,則好比彷如台灣過去歷史中的「二二八事件」,至今仍是比利時國內的政治禁忌,一旦碰觸,恐怕即被貼上極右派、新納粹主義者或是種族歧視的標籤。 此外,一向明顯站在法語派這邊的比利時國王亦對法蘭德斯運動沒有好感。法蘭德斯人也在戰後認為不需要一個只支持法語人的國王,而興起罷黜的聲浪,並有史上的「皇室問題」(Royal Question,1945-1950)發生,更加從國家最高統治層級,加深兩大語族之間的隔閡與對立【5】。 戰後重建階段,比利時的經濟發展開始向北邊的法蘭德斯地區轉移。十七世紀起以煤礦和金屬冶鍊為主的瓦隆尼區逐漸因為礦脈枯竭及勞工意識日漸抬頭,失去過往以來的競爭力,經濟蕭條。過去以農業為主的法蘭德斯區,則因發展新型經濟,又按人數比例取得國會多數席次, 終得以更加推動法蘭德斯意識。立法者自1960 年代起, 修定了過去在弱勢時期存在的許多不平等條款, 並在各地一掃以往法語人資源壟斷的陰影。學校教育也回歸母語教學。憑著法蘭德斯人來自務農背景的勤奮耐勞習性, 二戰後很快掌握國家經濟發展重心。新興工業區在法蘭德斯境內的安特衛普港,根特等重要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而「真正製造衝突的是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公,再加上心存不服的被支配者族群菁英的操弄。」(施正鋒,1998:60) 風水輪流轉, 經濟財政勢力日漸孱弱的南方瓦隆尼開始轉變策略,企圖藉堅持聯邦體制以便依法分享北方的財富。極端反之,北方則已經發展到足以完全脫離經濟狀況萎靡不振的瓦隆尼區, 得以隨自由意願決定成為一個獨立的自治體,甚至主權國家。 1950年代中期,各語族當中有極端族群主義政黨的成立,如「法蘭德斯人民聯合陣線」VL Volksunie,1954),法語區的「法語系陣線」(Front des Francophone-FDF,1965)、「瓦隆尼聯盟」(Rassemblement Wallon-RW,1968)等,將族群對立拉到正面與全面性層面。 1960年代末至70 年代,原先以聯邦體制為依歸,不分南北、法荷的傳統政黨,也因語族爭端問題, 陸續一分為二。即以繼續相同的政黨名稱,但各以荷文與法文來區分其代表的語族。如1968年基督教民主黨分成CVP和 PSC、1971年的自由黨分成PVV和PRL ,1978年的社會主義黨分成BSP 和 PSB。 3. 語族文化共同體(community)的劃分 1963年時,首先出現了語言文化區(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的邊界劃分法律。該法將比利時化為四個語言文化區:
此外在各語族文化共同區的接界上有所謂的「語言便利行政區」(Faciliteit/Facilite):即因語區分界地帶的鎮市級行政區中常有兩種語族居民混居, 為顧及此類行政區中少數居民的權利,當地政府接受少數語族居民經正式提出申請後,得以其母語書寫或收受官方文件(政府通告,戶籍,稅務資料,社會保險…),作為其與官方聯繫的公文書語言。 但是不久之後, 兩大語族文化共同體彼此合作的意願減低,自治意願增強。只是因為比利時不可分裂的觀念或因共識,或因現實狀況不允,尚未被當時雙方的人民與政治菁英積極提出討論。而面對語族區域愈見分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1970 年國會透過決議,以三個語言族群為基本區分原則, 重新將比利時畫定為三個語族共同體 (Gemeenschap / Communaute),首度將文化與經濟自主權下放到兩大族群自治區域中。至於爭議不斷的布魯塞爾,則遭暫時擱置。有關布魯塞爾的問題將在後面介紹。 1971年荷語區成立自己的文化事務諮議會,取代國會決定語區內文化和語言單行政策。當時諮議會的代表是從直選的上下國會議員中推選相當人數,另組成文化事務諮議會。這個文化事務諮議會對語族共同體內的文化和語言政策議定具完全主導權。其他公眾事務的自治立法權還是在國會。當時的問題是:語族共同體雖然透過語族國會議員組成的諮議會議決各項政策,卻沒有具備實權的共同體自治政府來執行決議,仍須透過國家級政府的內閣單位來執行。在不論法律上與實際上,共同體均無法對國家級閣員有效地要求執行文化事務諮議會所做出的區域層級決議。故諮議會存在的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另外,即便文化事務諮議會的議員是由語族共同體內直選產生的國會議員兼任,但其思考角度往往定位在國家層級以及跨語族共同體的層級,甚至自身涉及的利益關係上,不見得隨時將語族共同體權益為本位。 兩大語族在語言文化及政治社會觀念分歧愈趨嚴重, 南北地理區域之間的經濟實力落差更增, 諸多全國性法律已無法滿足不同語區居民的單獨需要,必須下放更多行政自治權到語區。於是在1980年的修憲會議中,議決決定在1970年代時期所劃定的語族文化共同體 (Gemeenschap / Communaute)之外,更進一步將比利時聯邦化(federalisation),劃定謂之「行政自治區」( Gewest / Region )的語族區域行政自治層級。產生了以行政自治權責來劃分出的:法蘭德斯行政自治區 (Het Vlaamse Gewest)、瓦隆尼行政自治區(La Region Wallonne) 為兩語族共同體的行政獨立位階找到新方向。至於布魯塞爾的定位,還是因雙方意見相左,妾身未明(附圖一)。 行政自治區得到公共衛生政策、殘障保護以及青少年福利等方面的行政自主權。自治區內有議會與自治區政府的機制,訂定與執行民意代表議決的自治法案。自治區政府閣員由議員(政黨協商)推舉產生,任命或罷免均由自治區議會決定。至於原有的語言文化區諮議會,則繼續從事語言文化政策方面的工作。至於混有荷語以及法語兩種語族的首都布魯塞爾,兩個共同體文化諮議會則各自負責其語族居民在布魯塞爾的語言文化政策事務,涉及雙語的部分則由國會議決,聯邦政府執行。 3.1 荷語文化共同體的語言法案 1971-1980年之間,荷語文化區文化事務諮議會通過了49項法案,多數法案都採被動地防堵法語人口侵入荷語區。比如1973年通過著名的「九月法案」,明定荷語文化區內的企業僱主得僅僱用荷語籍員工,並得僅以荷語訂定工作契約與各種法定文件,以保障荷語人在文化區內的基本工作權。鑒於當時比利時的資本家階級多數仍是法語人,該法案議決時曾造成法語人極力反彈與杯葛。到1978年時諮議會逐漸採取主動態勢,通過與民眾教育相關的「圖書館法案」,要求荷語區內所有鄉鎮區都設置荷文社區圖書館。總地來說,荷語文化區文化事務諮議會時期所制定的法案,旨在藉由各項地方語言政策的自治化,國家級語言政策的平等化,以及加強文化遺產的維護與保存意識,從社會基層尋回法蘭德斯文化的正常地位。 截至目前為止,「法語語族文化共同體」和「瓦隆尼自治區」仍堅持彼此為比利時聯邦制度下分別負責行政自治與語族文化事務的分離系統。而法蘭德斯自治區則在1980年憲改後,即將「行政自治區」與「語族文化共同體」兩個自治權合併在單一系統內實施。1993年憲改將過去自荷語裔國會議員間推舉法蘭德斯自治議會議員的方式,反向操作為地方直選。1995年法蘭德斯自治區議會舉辦首度直選,正式脫離上下議院間接代表制。其選舉制度是將法蘭德斯區內的五個省份,依人口比例劃成十一個選區,選舉118席設籍在法蘭德斯內的議員。另以特別條款保留6個席次給設籍在布魯塞爾首都自治區的荷語籍居民代表,以保障首都區荷語居民權益。自治區行政部門閣員是由當選議員間透過投票推選或是政黨協商產生。閣員人數以十一名為上限(目前是九名)。其中一個名額保障給布魯塞爾首都區出身的議員入閣。議員入閣後便失去議員身分,該議員空缺由黨內排名候選人遞補。行政自治區並依法推舉六名議員代表法蘭德斯區進入國會的上院, 為荷語人爭取聯邦政府層級的權益。國會於2002年7月才剛通過自治區政府可不透過聯邦政府,與他國直接從事國際貿易與國際合作的自治權。 4. 布魯塞爾首都行政自治區 布魯塞爾原位於法蘭德斯區中,在1830年獨立建國時由首任國王李奧波一世定為首都後,便由當時居於政治強勢的法語人逐漸進佔, 成為居民人口的多數。根據人口統計記錄,1846年(比利時宣佈獨立的十六年後),布魯塞爾的荷語居民還佔總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保有數量上的多數。到了1947 年(二戰後兩年)的統計,布魯塞爾的荷語人口降至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廿四,反倒成了少數族群。法蘭德斯人為防堵布魯塞爾繼續法語化,企圖設法收回布魯塞爾的管轄權力。而法語人自然不願失去在首都已佔有的優勢,導致雙方為此爭執不下。舉個簡單的例子:1972年荷語文化區文化事務諮議會在成立時,其設置地點即曾引發爭執。原來在當初選擇議事廳地點時,由於是國會議員兼任諮議會議員,因此議員建議不妨就地在國會議廈裡找個空間當作為會議廳。這個構想立即得到法語人的強烈反彈。當時法語人認為該諮議會不從荷語區裡的純荷語城市挑選一個城市作為諮議會所在,卻偏偏選上布魯塞爾的舉動,是一種公然的挑釁。 這種類似以布魯塞爾作為攻防戰場的爭鬥僵持到1988年,雙方終於妥協, 將布魯塞爾獨立成比利時的第三個自治區:布魯塞爾首都行政自治區(Het Brusselse Hoofdstedlijk Gewest / La Region Bruxelles-Capitale),並以雙語併行管理。 歷年來,法語自治區政府一向採取高分貝方式做政治喊話,重視布魯塞爾的法語居民權益。而為遷就現實經濟狀況,在實際事務上還是不得不僅以南方自治區內的經濟與社會自主權為首要目標,對布魯塞爾法語居民的重視程度偏低。反之,法蘭德斯自治區政府則期待爭回失土, 竭盡所能地在布魯塞爾從事各項建設與活動,突顯其為布魯塞爾原主的權力形象。還不斷以減稅,購屋貸款補助等方式積極地鼓勵荷裔人口回流布魯塞爾。 4.1 布魯塞爾的雙語問題 從多元文化主義(Pluralism)的角度來看,為了各不同種族或文化族群的存在和延續權利,在教育、文化、藝術、史料保存等方面實施雙語(多語)政策,有天賦人權基礎的絕對必要。其實這屬於硬體部分,只要經濟能力許可,並非難事。然而,要在居民生活環境中實際施行雙語(多語)公共政策,執行者或機制須在實際實施方面做好事前評估,並需時間與毅力不斷從經驗中取得改進的基礎,以維護雙語(多語)公共政策公平性,確實保障各族平等權利。布魯塞爾的經驗是:儘管荷語人極力在政策上推動雙語公共政策,但畢竟人口數量居於相當弱勢的荷語居民,儘管法律上的硬體保障已經取得。面對多數的法語居民(包括原有的比籍法語居民,還要再加上愈來愈多的外籍法語移民與流動人口),荷語居民的基本權益要完全落實維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依雙語法律的規定,布魯塞爾所有的公共行政機構,包括學校、政府單位、醫院乃至街道名稱都必須信守雙語原則。雙語政策在硬體(如街道牌,政府公告、公文書等)和法律規章上還算徹底實施。但是實際層面則存在許多難以掃除的盲點。就舉布魯塞爾首都區醫療系統的雙語使用現況作為一例證:現任布魯塞爾荷語自由大學(VUB -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校長Ben Van Camp博士,自該校醫學院畢業後,曾在1960到1970年代間於該校醫學院附屬教學醫院(Academisch Ziekenhuis,VUB)任職。當年親見醫院同僚多以法語從事醫療服務,導致前往教學醫院就醫的荷語母語者未如法律所示得到荷語醫療服務,於是與同僚聯合向院方爭取荷語患者應得的權益, 結果被院方驅逐。這樣的狀況發展至今,儘管已有改善,但是參照今年(2002年)六月號的「環京月刊」 (Rand Krant,2002:4-5) 所提出的數據顯示:目前布魯塞爾地區屬於財團法人經營(民營),不受語言法強制實施雙語看診與照護醫療服務的大學教學醫院有三所。 其中布魯塞爾荷語自由大學所屬教學醫院是唯一有荷語醫療服務的醫院。其他兩所教學醫院僅在接待處有雙語諮詢,進到急診或住院醫療部門,則無法保證是否繼續有雙語醫療服務。至於理應按照語言法提供雙語醫療服務的公立醫院,按實際調查顯示: 公立醫院當中只有10%的大夫因其荷裔背景,能以流利荷語從事醫療服務。多數公立醫院的問診、病歷紀錄或因醫院政策,或因醫療人員實際荷語能力不足,僅以法文為正式或慣用語言。再以醫療人口和醫院比例來看,布魯塞爾首都區以及環京區中有30%的荷語人需要到布魯塞爾的醫院就醫。純就比例來看,三所大型教學醫院裡有一所荷語醫院,百分之十的醫生可以荷語執行醫療服務,加上布魯塞爾語環京地區的荷語居民或醫生在正常狀態多半還是能以法語溝通,這個問題似乎可以勉強解決。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比如國人到美、澳旅遊途中遇有疾病就醫。假設在意識清楚情況下,即便我們的英文再好,語言隔閡是不可否認的溝通困擾,更不消說眾多不具備外語能力的單語患者。再舉布魯塞爾區及環京地帶荷語居民可能遭遇的急診送醫狀況: 救護車在正常狀況下,不會考慮患者所使用的語言,而只會將患者盡快送至最近醫院就診。按照上述的數據來看,荷語患者被送進法語醫院就診的比例會相當高。那麼可比國人被送進一家外國醫院一樣, 患者或家屬均不得不以非母語表達病情。患者與醫護人員可能在此緊急狀況之下,因溝通不易,產生問診不清,導致醫療失當,或至少醫療品質打折扣的結果。 4.2 布魯塞爾的法語化 過去歷史曾經存在過法語人的「語文沙文主義」(linguistic chauvinism),儘管這種說法不易以科學數據方法證實,但若能深歷其境體會之後,便可以明白此一不爭事實。本位主義強烈的法語人,向來以語言天賦不夠作為藉口, 但心中其實不願對其認為難以入耳的另個比利時官方語言用心學習。儘管法語人不斷在公共言論中強調比利時是一個國家,不得分裂。但是從語言實踐層面而言,不論平民或政治公眾人物中能夠使用流利雙語的法語人少之又少。許多人的共同經驗是:過了布魯塞爾所代表的語言區中線,進入北邊的荷語區內,居民多半能以簡單正確的法語和不會荷語的法語使用者溝通。反之,到了南邊法語區內,法語則是唯一的溝通語言。從現實角度來看,法語人語言本位的心態為其帶來的只有自我封閉與競爭力衰退。反之,佔比利時人口多數強勢,但居於語言弱勢的荷語人則向來較切實際,容易妥協。且具備雙語,甚至多語能力在比利時國內與國際經濟活動參與競爭。 布魯塞爾的法語化族群除了有原先的法語居民, 及趨於現實具備雙語的荷語人扮演重要角色外。更重要的「法語化」因素,是戰後因缺乏勞工而從義大利、非洲(摩洛哥)(附圖二)、中東(土耳其)大量引進的勞工移民、加上來自昔日比屬剛果(薩伊)的政治難民,陸續在不同時期進入布魯塞爾首都區。這些移民或本身殖民地語言便是法語,或在進入布魯塞爾後,因遭遇多數法語母語人或使用法語的外來移民,於是便成廣義的「法籍化」(frenchified) 法語使用者。當然更不能遺忘由於歷史認知不足,始終誤將法語視為比利時國語的數萬歐洲公務員、外國使節人員【7】及其家屬,逐漸在布魯塞爾首都區形成一個龐大的廣義法語族群(francophone),形成布魯塞爾的法語化現象。 這種法語化現象在現實造成的社會問題,可舉最近(2002年六月)發生的案例說明:四名未成年阿拉伯裔青少年以取樂為由,在街上將一名比籍老者毆打致死。老者之妻代表死去夫婿到法庭提出告訴,並出庭控告。審理法官與被告均為法語母語使用者,鑒於數量強勢,所有庭訊過程以法語進行,但請有一名法-荷口譯伴隨原告。法官與四名阿拉伯裔少年在庭訊時,不脫法語人說話一向極快的習慣, 無顧原告與法庭口譯經常因不及即時精準翻譯辯護與質詢內容,導致原告難以精確掌握開庭審訊內容。加上四名被告聰訐地將所有動機與責任推給年紀最輕的十歲少年。法庭最後以口頭訓誡為懲處,當庭將四名青少年無罪開釋。這個案例顯示及引出的問題,不僅是首都法語化現象中,荷語人勢力更加減弱。還有中下階層外來移民因種種原因,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如得到白領階級的優渥工作),導致心理不平衡,動輒指責當地居民(特別是針對和他們語言不同的荷語人)對移民抱有種族歧視心態,便以頻繁的街頭犯罪方式發洩情緒。在原本已經相當複雜的國內語族紛爭問題中,製造更多複雜的影響因子。 首都地區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具備流利雙語工作能力的荷語人,理應會大量進入布魯塞爾找尋機會與落腳居住。事實則不然。除了上述的社會治安問題之外,已經在首都得有工作的荷語人對於首都的語言環境多數興趣缺缺。畢竟在下班後能回到自己母語地區過正常的社交、購物家居生活,要比還要繼續用外國話(法語)來得誘人。因此,布魯塞爾在正常上班期間,每天有四十萬的通勤人口。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從法蘭德斯各個角落到布魯塞爾來工作的荷語人。其中並不乏火汽車日通勤時間總長達四小時者。 近年來法語區政黨不斷推動外國居民與比利時國民同享地方自治權的主張:意即不論是否擁有比利時國籍,凡住在比利時國境的成年人,均應享有選擇地方民意代表的權利。這個議題則一直被荷語人視為法語族群政黨意圖假借民主,企圖得到更多親法語系外國居民的選票,以達民主「法語化」布魯塞爾的目的。荷語人擔心的是:當允許這些親法語人的外國移民具備投票權後,荷語人口將更成為少數。總有一天,法蘭德斯會因此失去布魯塞爾,而讓布魯塞爾成為法蘭德斯區中的法語櫥窗。 5. 環京地區(De rand)與其語言便利特區(De faciliteitengemeenten) 的語族攻防戰 比利時的語族衝突從最早的聯邦層級,演變到文化自治區的誕生,再到行政自治區的分離,最後是布魯塞爾首都區的脫離自治。首都區居民多國化後,原先雙語之爭議題已逐漸被其他因素與議題所吸收和淡化。此間,真正的純語族戰爭並未終止,而仍然在首都週邊的鄉鎮裡引爆。 為顧及基本人權(法語人使用的理由),鑒於語區邊界的許多荷語鄉鎮實際已住有相當數量法語人口。按照語言邊界劃定時的規定,可由居民以書面方式向地方政府申請特許,合法長期取得以法語接收或是至少以法語回覆公文書的權利。這個便利條款,在當初荷語人簽署同意的心態是期待混居在荷語自治區內的法語人能主動逐漸加強荷語能力,以便融入荷語區社會(荷語人使用的理由),荷語區自治政府便將這些邊界型鄉鎮定為所謂「語言便利特區」 (De faciliteitengemeenten)的特殊待遇。 再者,就地理位置言,布魯塞爾可比擬以往的座落在東德境內的柏林。柏林四周有柏林圍牆作為東西德分界。布魯塞爾則有週邊荷語區鄉鎮包圍,作為語言區域防線。為了確保語言區域邊界不再向法蘭德斯區推進, 居於語言弱勢的荷語區自治政府又將首都外環的十七個行政上歸屬於布拉邦法蘭德斯省(Brabant Vlaanderen)的鄉鎮,歸劃為「環京地區」 (De Rand),在其中嚴格執行荷語單語政策,或者以上所提的「語言便利特區」條款來捍衛語區疆界(附圖三)。布魯塞爾荷語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 VUB) 社會學教授R. Janssen 把這個議題喻為<在教堂裡以上帝之名詛咒的粗話>【8】。以下不妨舉幾個最近發生的案例: 布魯塞爾南部的「語言便利特區」市鎮Drogenbos市政廳官員向來有刻意偏袒法語人的紀錄。今年(2002年)該市市政廳逕行宣布凍結今年失業救助金的發放。詳細經過是依語言便利特區法律,失業金的發放通知應以荷文公文信發到每個居民家。居民得以荷文或法文回覆是否提出申請。據統計該市失業人口中法語人佔了全數的90% (因缺乏「雙語」能力,無法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市長曾以此為由向荷語區政府建議彈性處理,以法文向全市居民發信。荷語自治區政府所屬單位未做回覆。於是該市市長則以既不得違法以法文發函,又不依法按時以荷文發函,逕自凍結該款的發放,並將責任歸咎於荷語區政府罔視居民權益。根據分析, 該市政府不過是希望利用語言便利權議題的爭議,變相阻止隔鄰首都區的失業人口湧入該市領取失業金, 增加市政財務負擔,故藉此事件凍結失業金的發放, 以便讓打算自布魯塞爾遷入的外地人知難而退。(環京月刊Rand Krant,2002:12) 另則被「京環月刊」譏為比利時典型「超現實妥協法」(Compromis a la belge)的事件是在環京地區東環的Wezembeek-Oppem市鎮。市政府依法每年向居民寄發垃圾處理費繳費通知單。該通知單依語言法律規定應以荷文書寫。自治區政府經查獲知該市政府於1998年處理該稅徵收時,違法逕自以法文發出該通知給該市居民,於是要求該市以退還所有徵收金額給市民,做為懲處方式。並打算派遣調查小組清查所有市政府發出的文件檔案,調查是否在其他業務方面亦有違法事實。法語自治區社會黨主席獲知該事後,立即串聯法語區其餘政黨,以發動語族政治危機為要脅,要求荷語自治區政府收回懲處成命,並不准派遣調查小組。經協商結果,荷語區自治政府為避免事端擴大,妥協結果改要求該市市政府在得完全保留全額所收稅款情況下,重以荷文開立一張以當年為繳費年份,但徵收金額為零比利時法郎的繳費通知單,並附上書面信函解釋原委。算是在面子上懲處了該市官員, 並且保障了法律的尊嚴,結束整個了這個比利時經常所謂的「超現實事件」【9】。(Rand Krant,2002:2) 四、結論 海姆(Hymes 1964:xxiii) 引出「語言人類學」 (linguistic anthropology)一詞,即以社會文化定位來探討解析語言使用的學門, 在北美地區廣為學者採用。語言使用與社會演變之間的關聯成為一項跨學門的研究題材。在全球化與區域化的交互作用過程中,多元語言社會的推動與弱勢語言的保護不僅是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各家共同感到興趣與思索探討的問題。時至今日,就全世界語言人類學者而言,逐漸理出兩種研究心得: 一是關於語言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工作,仍然需要繼續下去,以提供給研究學者作為資訊蒐集與理論建立的基礎。在田野調查之外,由歐洲學界重視的「接觸語言學」 (contact linguistics):即涉及範圍特定在社群認同形成、語言讀寫具體化、語言使用權運動、及勞工薪資經濟生態及爭取經濟資源分配等議題中的語言使用研究。接觸交涉對象牽扯到政府、其他社群、私人企業、官僚體系機構等的研究方式,成為一種主流。 另個心態是脫離過去「挽救語言學」(salvage linguistics)的觀念。意即在發現一個語言即將面臨消失的時刻,不應抱著期待能挽救該瀕臨絕跡語言的負面心態,而應投注較多心力在研究該語言之所以面臨絕跡的社會和文化現實因素,以便汲取更多的經驗,對抗這些窒扼語言生存的因素。 比利時語族爭端問題確如薇特和梵費爾特霍文所言,是世界罕見語族衝突的試煉個案。時至今日,比利時法語人是否還仗持法語人自歷史中得來的某種共通的語言優越感? 在現實事務上,不論是否因其天生語言能力不佳或是意識型態使然, 他們依然多半與法語系國家或區域進行合作(如法國、瑞士、加拿大的魁北克等),然後才是其他語言國家。從另一個角度看,在面對歐洲與世界(特別是美國)其他國家正無法抗拒的全球化趨勢, 似乎只有比利時,法國及其他地區的法語人以法語族群(les francophones)還不斷做著挽救語言自尊與保障語族文化的努力。至於這個理想是否如螳臂擋車? 明擺在眼前的是許多努力與毅力,還有面對挫折的勇氣。 回到比利時荷語人所堅持的, 也許可說是為了遠自建國以來交繼下來的一口氣,或捍衛最後一片語族文化疆土的心情。在其內部政策上有保守派與自由派各以不同理由,達成共識地在國內議題上與法語人拉鋸。假若將法語人在全球化社會當中對抗英、美國家的模式來看,荷語與法語語族的爭執相較,似是同一個議題在綜觀(macro)與微觀(micro)的不同格局下的相同理念與堅持。進入法蘭德斯社會內部觀察,一件令人訝異的現象是:居民受全球化的影響遠超過南邊故步自封的法語區。打開電視頻道和收音機,幾乎都是英美的電影、電視影集以及流行音樂。真正屬於荷語人自製的節目和音樂歌曲少得可憐。而現在政治菁英所堅持的語族認同,其實正面臨一個過去外表口號與今日現實深層之間兩相矛盾的兩難。 在兩大語族爭端下,另外還有一個遠在比德邊境,居民僅佔比利時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德語區域。儘管依語言法有所謂的德語語族文化共同體的設置, 在行政上卻還是歸屬在瓦隆尼自治區(法語)支配, 僅以聯邦政府體制下的三級行政機制運作其語族事務。歐洲兩次大戰均由德國發起, 法語人對德國的仇視已在先前的章節提過。且在這共同體區域的部分土地還是戰後比利時以戰勝國向德國索賠而得的領土。對於也曾經歷過「肅奸報復活動」經驗的德語區居民,十分「自覺」自身的實力與現實需求。在族群政治議題上所採取的姿態,向來比至少在人口方面佔多數的荷語人要低調謹慎得多,以免引起尤其是法語族群的強烈反應,或使得荷語族群借題發揮,藉故將德語區捲入其與法語族群的鬥爭,增加無謂的困擾。在其語言文化的保存與發展議題方面,比利時學者P. Nelde和J. Darquennes (2002)在最近一篇以比利時德語區新聞媒體語言使用的研究報告中指出:該語區在報紙與日常語言中所使用的德語已經轉化成一種混雜了德語、荷語與法語的德語主結構語言。這明顯顯示而該區在語言絕對弱勢的地位下【10】,居民為了爭取更多在德語區外的認同,所不得不做的讓步而已。此外,為爭取更多外地就業機會,德語區內幾乎人人是三語(trilingual)使用者。居民中的壯年人少數還留在比東故鄉,多數都前往法語區,首都布魯塞爾和跨越邊境到德國的鄰近城市如亞琛(Aachen)、科隆(Koln)等城市工作。 1984年台灣教育部曾函內政部,認定教會在山地鄉與偏遠地區使用方言與羅馬拼音傳教,居心叵測,憂慮因此導致妨礙國語文教育之推行。1985年台灣長老會機關報「台灣教會公報週刊」的對此回應:
比較學者海姆(Hymes,1985:vii)所說:「即便世界不再有某個角落存在政治宰制或社會階級劃分的情況, 語言使用的不平等卻仍將存在…」
和學者黃宣範(1993)在著作中所引用一段百貨公司店員的話:
「我是個百貨公司的店員,會說國語、台語。不同的顧客,我就使用不同的語言,我要讓顧客有某種『信任感』,所以隨情況不同而用不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我通常用國語跟年輕的顧客交談,因為跟他們用國語交談比較時髦,比較『高級』。可能的話,夾雜一點英語也很有利於我的推銷工作。如果顧客不是年輕一代的,我就先弄清楚他(她)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我通常是先以國語開口,然後根據他們的回答,決定是否改用台語。但並不是凡是顧客是本省人我就用台語。越受過教育的顧客,我就越用國語。我在家大多用台語。但小孩常常喜歡用國語講學校的事,我也只好用國語跟他們交談。」 在面對語族間的共存議題上,堅持自己的母語有其絕對的必要,旨在以人文與道德角度求取保存良好的傳統價值。至於面對現實爭端與延續未來的需要時, 與其「不得不」,不如以「為何不」的多元主義態度,將實際事務與意識型態的包袱分開,才能妥善處理複雜的族群共存議題。
最後,從族群議題研究的角度來看:比利時與台灣兩國在族群議題方面有諸多值得對照比較之處。未來值得繼續進行的研究方向,可從雙方的族群形成原因、各族群特性,以及影響雙方族群問題的社會內部與外部國際因素等做詳盡分析與比較。僅以非常概括地來比較雙方的族群議題之異同,可從雙方相似的部分,比如說國家的形成背景、族群衝突與融合發展過程、族群數量,以及新移民的加入等做類似比較; 至於相異的部分,則在族群人口相對比例、族群的混居與雜居、影響族群爭端的國家內部因素與外部壓力等方面等做研究比較。
本篇論文限於篇幅,僅以比利時族群議題的發展過程與現況做紀年體式描述與介紹。期待為後續的台灣-比利時族群議題比較研究,引發興趣與累積基礎資料。
參考書目與網站 Corcuff, Stephane, (ed.), 2002, Introduction, In Memories of the Future, Armonl: M.E. Sharpe Hymes, Dell, 1985, Preface, In Language of Inequality, N. Wolfson and J. Manes (eds.), v-viii, Berlin: Mouton Nelde, Peter and Darquennes, Jeroen, 2002, Linguistic variation from contact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Brussels Ricento, Th. (ed.), 2000, Ideology, Politics and Language Policies Focus on Englis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Witte, E, Alen, A. Dumont, H. Ergec, R. (eds.), 1999, Het statuus van Brussel / Bruxelles et son statut, Brussels: Larcier Witte, Els and Van Velthoven, Harry, 1999, Language and Politics – The situation in Belgium i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ussels: Balans VUB University Press Wolck, W., De Houwer, A. (eds.), 1997, Pluriligua XVIII– Recent studies in contact linguistics, Bonn: Dummler "Taalgebruik in de rand en in Brussel", In Rand Krant, P25, Maart 2002, Jaargang 6, Nr. 3 "De wereld draait niet (meer) rond Wezembeek-Oppem", In Rand Krant, P2, April 2002, Jaargang 6, Nr. 4 "Brusselse gezondheidszorg nog altijd in hetzelfd bedie ziek", In Rand Krant, P 4-5, Juni 2002, Jaargang 6, Nr. 6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 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黃宣範, 2000, Language, Identity, Conflict: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廖招治, 2000, Changing dominant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equality in Taiwan since 1987,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林碧炤,1997,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 曹逢甫,1997,族群語言政策 – 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比利時政府網站: http://www.gov.be 註釋 【1】除法、荷兩大語族外,事實上還有一個更為弱勢的德語族群,存在於比利時東部,與德國接壤的區域。 【2】時至今日,比利時荷語區內居民使用的語言仍然按地理位置不同,混有程度不同的外來語和口音。比如西法蘭德斯地區因與法國接壤,混有相當多的法語字; 北部的安特衛普方言則與荷蘭的荷文用字語口音相近。布魯塞爾附近所使用的語言則是混有荷語與瓦隆尼法語方言的布魯塞爾語。 【3】此指的中產階級(bourgeoisie) 並非現今所謂的(middle class),而是因為工業革命與封建社會逐漸崩解時,因為經商致富而得到社會肯定其地位的「有產階級」,但當時相對於貴族與平民,他們被稱做「中產階級」。其中當然不乏所謂的暴發戶。 【4】學者廖招治曾以過去台灣的台北與下港,台北市區與台北市郊南部對於國語與台語使用的意識型態。描述此一「語言沙文主義」現象。(Liao,2000: 181) 【5】直到較具親和力的比利時第五任國王- 柏多安國王(King Baudouin)加冕多年起,鑒於皇室英對其國內語族應一視同仁,才將每年告全國人民文告,以法、荷語雙語發表。 【6】也是事實上比利時境內唯一的雙語區域。 【7】台北代表處曾經常接獲荷語居民電話抱怨,批評代表處中除當地雇員外,駐外人員中完全沒有荷語能力。甚至連全球網站也只有法文,沒有荷文網頁。明顯輕視荷語居民的存在與權益。 【8】vloeken in de kerk,意指不得公開談論的禁忌。 (環京月刊Rand Krant,2002) 【9】比利時曾經出過著名的超現實畫派(Surrealism)巨匠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畫作內容奇異如夜中有日,日中有夜,或是鏡中有人,人中有鏡等所謂超現實影像。比利時人便以此作為嘲諷國內政治爭端的字眼。 【10】比利時德語文化區的居民甚至不再受到隔鄰德國人的認同,成為邊界的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