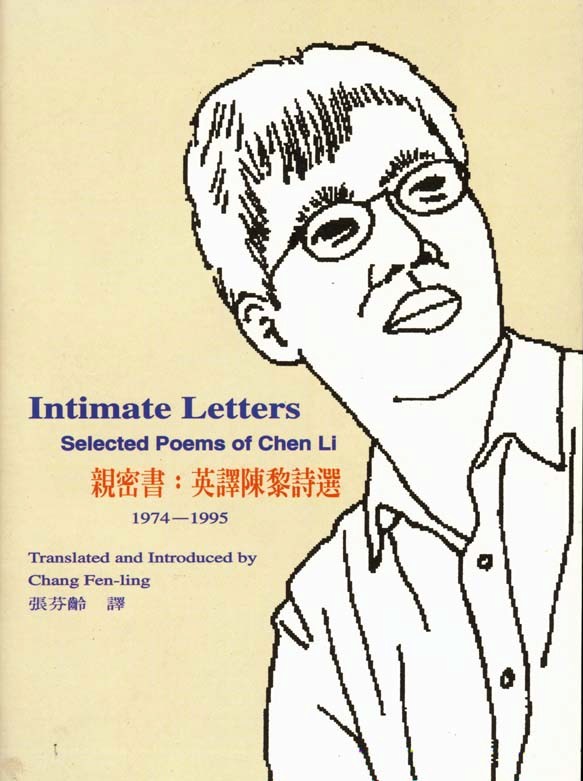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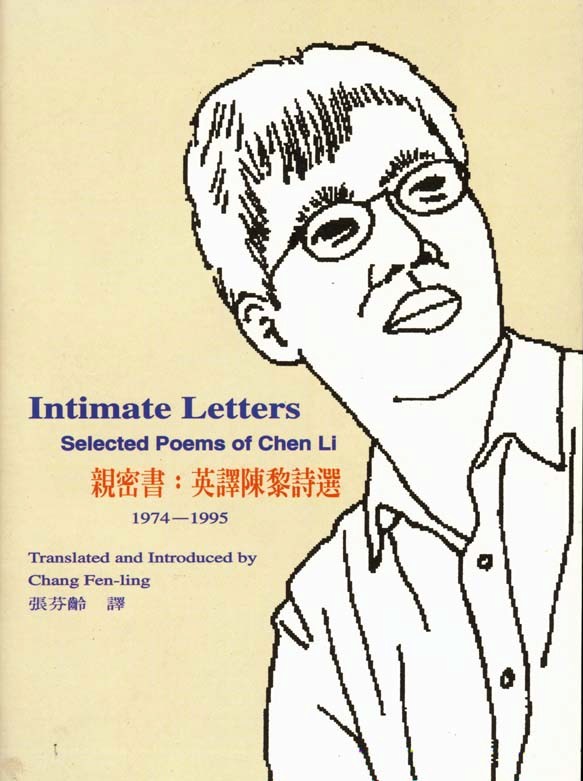
陳黎(本名陳膺文,1954 年生)是當代台灣詩壇極具代表性的詩人。他自一九七O年代初期開始寫詩,迄今出版有七本詩集。在二十餘年寫作生涯中,他的詩風歷經數次轉型。原創性,多樣性,機智與深度一直是他所深切關注的。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駕馭意象的嫻熟能力以及對多樣技巧的試驗。
生長於台灣東岸的小城花蓮,陳黎從他的家鄉得到許多靈感。在詩集《動物搖籃曲》的後記裡,他說:「世俗難道不是我詩作最大的主題嗎?……我始終不能忘懷這地上居留的卑微與鄙俗。」從小城諸多鄙俗、曲扭的生活斷片,他認識到現實的缺憾和錯亂。在第一本詩集《廟前》(1975),他一方面天真地企圖透過對童年、家鄉及母愛的依戀和書寫,來守護自然;另一方面,則以諷刺的手法痛鎚現代生活中種種乖謬與非人道的現象。不論以何方式,小人物地上生活的困境與尊嚴是他關注與同情的焦點。
在第二本詩集《動物搖籃曲》(1980),陳黎不再是嘲諷的寫實主義者,他成為浪漫的象徵主義者。對自然的想望和對城市生活的嘲諷如今轉化成一種對生命和時間較廣博的情思。他營建想像的世界,捕捉剎那美好的經驗,試圖在有限、脆弱的現實中尋找出某種可供規劃的秩序以對抗凌亂的世界。〈在一個被連續地震所驚嚇的城市〉一詩生動呈現了人類在地球上錯亂而荒謬的處境。陳黎對生命時抱陰暗的看法:世界是一個監獄,每個人生來即是囚犯(〈囚犯入門〉);人們無法免於恐懼,一場「驟雨」即可將人的安全感沖盪殆盡。但陳黎並非悲觀主義者,他對生命中的形形色色仍充滿好奇與想像,並且能夠從中汲取喜悅。這本詩集裡有一個反覆出現的母題——世界是一個充滿戲劇性場景的劇場。在〈魔術師夫人的情人〉,陳黎讓意象一個接一個生動自然地流出,烘托出魔術師夫人詭譎的性格以及變化莫測的魔術氣氛;在〈我們精通戲法的腹語學家〉,他更是大量地使用意象,想把腹語學家的戲法一無所遺地展現給讀者。而詩人自然也證明自己是一位意象的魔術師。
陳黎對跋涉於人生,被不安與恐懼所苦的人類充滿關懷。他們「被連續地震所驚嚇」,受時間壓迫,被慾望所苦惱(〈房子〉裡的情婦);他們為不可復得的童真哀悼(〈在學童對面〉裡的老師),卑微地渴求人性的尊嚴(〈小丑畢費的戀歌〉)。陳黎對人類困境、苦難的悲憫與諒解在標題詩〈動物搖籃曲〉中清楚顯示出。陳黎小心地選擇意象與語調,間接地呈現主題,成功地避免了濫情。搖籃曲中的世界是安靜詳和的,但那是個「沒有音樂的花園」,可視為永恆睡眠的園地——墓園(灰濛濛大象沈重的步伐暗示送葬的行列)。在這首詩(如同在〈黃昏過蘇花公路送癌症病人回家〉),陳黎反諷地指陳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死亡似乎是人類苦難唯一的解脫之道。
陳黎的人道關懷在一九八O年獲時報文學獎詩首獎的〈最後的王木七〉中表露無遺。在這首長詩中,陳黎展現了他敘事與抒情的詩才,在理性與感性、藝術與現實間,找到完美的平衡。詩中的說話者王木七,是礦場災變的死難者。透過他,陳黎企圖呈現礦工的生活,將他們的恐懼與夢魘,哀愁與徬徨,夢想與憧憬展現在我們眼前。陳黎巧妙運用了對比:我們聽到王木七的亡魂追敘災變的慘狀,我們聽到罹難者的家屬令人心碎的哭泣,我們看到礦工們愁慘的生活以及宿命的認知,但我們也看到他在心底描繪的烏托邦夢土;我們看到十六組黑色的意象交織而成的輓歌,但我們也看到王木七寫給妻子,充滿柔情的家書;我們看到礦工們的困境,但我們也看到詩人嘲諷地批判漠視這群小人物苦難的人們。生之困頓和死之解脫的對比遍佈全詩。陰暗和明亮的意象交替出現,互撞互盪,相輔相成,全詩的張力如是形成。
在第三本詩集《小丑畢費的戀歌》(1990) 中的「暴雨系列」,陳黎在停歇近十年後,開始傾瀉他對腳下土地的關懷——它的歷史,它的文化,它的社會,它的人民。個人對時間、生命的思索被對台灣歷史的省視以及台灣經驗的追索取代了。他寫「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在祖國的懷抱裡被祖國強暴」的苦難人民(〈二月〉);他以蔥做為台灣本土文化的象徵,甘心回頭重新認識、珍惜自己生長的環境——它的歷史,文化,藝術,它的一切(〈蔥〉);他借台灣前輩雕塑家黃土水的作品《水牛群像》,呈現出台灣人民苦難又堅韌的形象,委婉地抗議社會的不公,並且窺探島嶼秘密的夢想(〈牛〉);他憧憬美好的未來:繼起的世代能領受傳統和土地的價值,活在一個包容、接納不同聲音和理念的自由、公平的世界(〈為吾女祈禱〉)。
陳黎擴大了家鄉的版圖,使之成為許多意象和象徵的發源地,而太魯閣無疑是他總結台灣經驗的一個理想的象徵。〈太魯閣•一九八九〉,雖非陳黎最長的詩作,堪稱他企圖最龐大、視野最寬廣的作品。在這首詩裡,陳黎描繪太魯閣峽谷瞬息萬變、難以捉摸的多種面貌,暗示台灣複雜多變的命運;他企圖引領讀者回顧台灣的苦難,追尋它失落的文化,並且體認到台灣乃是一融合不同族群、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的熔爐。隨著時間的流逝,太魯閣或許再也無法回復到她最純粹、最本真的面貌,但新的生命帶來新的溫馨、活力、和諧和甘美。全詩以太魯閣巖頂禪寺的梵唱作結,詩人悟出了生命大道:當人心壯闊如太魯閣的山水時,人間的愛恨、悲喜、成敗、苦樂都能一一被沈澱、包容或拂平,一如生活在太魯閣懷抱中的人民,接納了種族的差異和生命的甘苦。
「暴雨系列」之後,陳黎在第四本詩集《家庭之旅》(1993)裡,為其詩風及題材找到了新的方向。他卸下沈重的歷史與文化省思,轉向自己的生活經驗尋求靈感,以樸實平易的語言和節制的語調,思索生命的某些質素。在由七首短詩組成的系列詩作「家庭之旅」裡,他把一段悲苦的家族史轉化成為若干動人的生活剪影。藉由這些詩作,陳黎證明自己不僅僅是富使命感的悲憫詩人,同時是一個溫柔深情的人。此組詩作瀰漫著暗示悲苦、陰暗及破碎生命情境的意象,銜接整組詩作的一個共同主題是生命的缺憾。然而,我們也看到了和這些陰鬱意象並存的溫暖的生命質素——親情,夢想,堅毅及包容。有了這些,憂傷的母親們可以沈默地擁抱「焦急的火」和「重新回來的浪」(〈家庭之旅〉);窮苦人家的孩子會全力護衛他們的書包,因為那是未來希望之所寄(〈樓梯〉);鞋子破了的流浪者在泥濘的都市雨夜憶起美好的昔日(〈鞋子〉);年老多病的祖父在窄屋等候天黑時,「彷彿聞到了花香」(〈花園〉)。在〈騎士之歌〉,陳黎透過圓形的意象,表達出他對生命的諒解和包容。手鐲,戒指,項鍊一方面象徵無可逃脫的生命枷鎖、家庭束縛,一方面也象徵世代相連、延綿不斷的人間情愛和生命承諾。
陳黎自日常生活擷取意象和場景。記憶像一條「冬天用過,夏天忘掉」的圍巾(〈親密書〉);在十字路口遇見母親,讓他想起親人間似近還遠、似遠實近的關係,這也是人際關係的具體寫照(〈相逢〉);在進行捷運工程的城市,孤獨的旅人像一枚硬幣掉入「巨大而混亂的公用電話」,企圖「撥出自己」,卻自退幣口排出(〈捷運系統〉)。在我們每日喝水的杯子裡,他看到一條流動著時間陰影的河流,生命來來去去,就像茶花或茉莉花的開落(〈陰影的河流〉)。對陳黎而言,生命本身即是一場精彩的魔術,我們全都生活在瞬息萬變的魔術世界中——沒有永恆的事物,並且事物的表象和本質不盡相同(〈魔術師〉)。因此,身為語言魔術師的詩人,用一個閃現的意念,一個突發的情緒,或一首樂曲變出許多動人的生命場景。在〈給梅湘的明信片〉一詩的註裡,他引用了日本作曲家武滿徹的一段話:「音樂的喜悅,基本上,似乎與哀愁分不開。那哀愁是生存的哀愁。越是感受音樂創作之純粹喜悅的人,越能深體這哀愁。」這也適用於陳黎的詩創作。眷愛人間的他,對存在的哀愁有著深刻的體會。
這本詩集裡最有趣的一首詩也許是〈為懷舊的虛無主義者而設的販賣機〉。陳黎設計了一個遊戲讓讀者玩。但有趣、好玩並不是他提供的唯一東西。他似乎暗示我們:現代人生命裡失落了某些自然的質素,諸如母奶,浮雲,蟲鳴,鳥叫。但另一方面,他提供了好幾種烏托邦讓讀者選擇。那會是多麼奇妙的世界啊,如果這些東西隨時可得——熱母奶,大包的浮雲,持久型棉花糖,罐裝白日夢,附鳥叫的香水,自由與和平的大麻,白色的月光原子筆!一個理想主義者才能發明出這種給懷舊的虛無主義者的販賣機。
陳黎的第五本詩集《小宇宙》(1993) 收錄了一百首三行小詩。以日本俳句為原型,他並沒有嚴守俳句的傳統規格,卻為它加上當代的趣味,試圖探索詩的新可能。以如是簡潔、精鍊的詩型激發讀者的想像,對所有詩人確實都是一種挑戰。這些短詩,在最好時,是自身俱足的小宇宙,讀者可從中獲得自日常生活發現新意義與新感性的樂趣。陳黎似乎具有從每一樣東西發掘詩意的洞察力。遙控器,旋轉的骰子,耳屎,九九乘法表,回力球,一顆痣,豆漿,水龍頭,發瘋的女人,一雙涼鞋,按摩院門外的毛巾,盲人的合唱,勃起的陰莖,屋頂上的天線,抽水馬桶——這些東西和秋風,孤峰,雲,星,草,巴爾托克,巴爾扎克,波特萊爾,學童,項鍊,藍絲巾,眼淚,哀愁,激情,愛一樣富有詩意。透過《小宇宙》,我們偷窺大世界,並且發現極大的閱讀樂趣。曾有批評家將俳句比做一口沈寂的鐘,說讀者得先學做虔誠的撞鐘人,才聽得見空靈幽玄的鐘聲。的確,俳句每透過意象含蓄地暗示,而非直言——它的完成有賴詩人的想像以及讀者心智的積極參與。讀這些詩讓我們想到佛洛斯特所說的:「一首詩應始於喜悅,終於智慧。」
像所有自覺的作家和藝術家,陳黎不甘定於既有的風格。他總是擺盪於不同的藝術座標,試圖尋出理想的位置。因此,我們看到他不同的詩風,並且分享不同詩集裡的新樂趣。但他的詩集從沒有一本像最近的《島嶼邊緣》(1995) 那樣給予我們這麼多驚喜。這本詩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在於其對詩形式的試驗,我們可在選譯於這本詩選中的圖象詩裡見到(很可惜本詩選只收錄了五首陳黎的圖象詩,因為中、英文化背景與文字的巨大差異使翻譯大為不易)。在〈戰爭交響曲〉這首詩,我無意將中文翻成英文,因為此詩的魅力一經翻譯將大大流失。那些中文字(「兵」,「乒」,「乓」,「丘」),以及帶有特殊視覺效果的詩的形式,已自我表明意思。這不僅是一首詩,也是一幅充滿聲音與意義的圖畫。在第一詩節,我們看到軍容壯盛的部隊邁向戰場;在第二詩節,我們看到悲慘的戰爭場面:有些士兵受傷,斷了腳,有些也許戰死,如穿插其間的空白所暗示。在最後一個詩節,所有士兵似乎再度集合,然而它們或許缺臂斷腿,或者埋身墳場(「丘」視覺上暗示斷腳的戰士,字面上的意思則為小土山,中國人埋葬死者之處)。山丘雖無言,卻對殘酷的戰爭做了最強烈的控訴。〈戰爭交響曲〉成功地結合了影像、聲音以及中國文字的特質,是對戰爭沈默的批判,是對受難者悲憫的輓歌,也是對中國文字的致敬。
在許多詩,譬如〈齒輪經〉,〈吹過平原的風〉,〈一茶〉,〈秋風吹下〉,陳黎展現了他對文字的敏感以及「再起動」文字的功力(同樣,很可惜地,中、英文間的障礙使英文讀者不能同享陳黎在中文裡豐富呈現出的機智與巧思)。陳黎將一些中國字和成語,自它們被習以為常、視若當然的傳統意涵解放開來。他試著將它們帶回語字的源頭,引領讀者從遺忘已久然而全新的角度詮釋它們——如同他回顧他母土的歷史,不僅為了「再發現」,也為了「再開發」其意義。
對台灣歷史的省思一直是一九八九年以來陳黎詩作的主題。在〈蔥〉這首詩,陳黎重新審視他在島上的居留,企圖在歷史與個人生命版圖重新定位台灣。在〈太魯閣•一九八九〉,他把家鄉花蓮看做是充滿生命力的象徵——這生命力來自族群間的混血與包容;在〈花蓮港街•一九三九〉,他試著重組散落的聲音以及歷史場景,將這個新生城市動人的氣質和形象顯現在我們面前。在〈福爾摩莎•一六六一〉,他帶我們進一步回到十七世紀,當時台灣仍被荷蘭所據,而行將歸鄭成功(一六六二年逐走荷蘭人,企圖以台灣為反攻大陸基地的明朝將官)統治。陳黎在詩中大膽結合了兩種看似衝突的元素——嚴肅的歷史主題,以及暗示官能與性慾的意象——由是造成此詩的後現代趣味。此詩的說話者是一名帶著種族優越感,且對自己在島上的成就志得意滿的荷蘭傳教士。他扮演著雙重角色:殖民者兼教化者,同化者兼被同化者。陳黎對這些外來的侵入者並無敵意,他甚至在他們身上找到某些人性的東西。在這首詩近末尾處,荷蘭傳教士說:「……我一直以為我們是╱住在牛皮之上,雖然那些拿著鉞斧大刀╱乘著戎克船舢板船前來的中國軍隊╱企圖要用另一張更大的牛皮覆蓋在╱我們之上……」這諷刺地暗示著:如果不能尊重原住的居民,任何政府——即便由血緣相近的族群所操控——可能只是另一種形式的侵略或殖民。從〈蔥〉到〈福爾摩莎•一六六一〉,隨著陳黎對台灣歷史的深入探索,他對台灣的定義也變得更加寬闊。在尋根的過程中,他發現台灣的活力其實在於它是一個熔爐或調色盤——融合多元的族群與文化元素。那位十七世紀荷蘭傳教士無疑是陳黎台灣聯合家族的成員之一。政治的衝突在詩裡得到了完美的解決。
在政治與藝術的拔河中,後者的力量絕不容忽視。在中國畫家李可染身上,陳黎找到活生生的例證。統治者用「草木皆兵的恫嚇」統治藝術,而藝術家卻用「如削如劈的筆墨」解放政治(〈秋風吹下〉)。對藝術深信不移的藝術家,悲壯地讓自己在政治的壓力下存活下來,尊榮地成為統領美與真理國度的主人。陳黎頌讚藝術對政治的勝利,但他深知隱藏其後的悲劇本質。他從來不是一個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在〈憑空〉這首詩,他把詩人比做一隻蜘蛛,
佔據幾枝樹枝
陳黎在一九七六年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回到自己的家鄉(「島嶼邊緣」)教書,並且一直留在他的「海岸教室」。這名迄今未曾旅行國外的詩人,曾經在一篇題為〈旅行者〉的散文裡如是說:
只要對世界懷抱渴望我就隨時在移動。我知道坐在教室裡的我的五十位學生是五十本不同的旅遊指南,指向五十座不同的城市;我知道我每天在街上,在市場邊碰到的人,他們的心跟這世界所有的名勝古蹟一樣豐富。我…在我的城複製所有的城,在我的世界城旅行全世界。 透過閱讀與聆聽,他讓自己和世界保持相當的聯繫。他寫他喜歡的作家,音樂家,藝術家,並且把許多詩人的作品翻成中文。在陳黎自己的作品裡,我們可以找到這些人的回聲:智利詩人聶魯達(譬如在〈最後的王木七〉與〈太魯閣•一九八九〉),十八世紀日本俳句大師小林一茶(在〈一茶〉與《小宇宙》),德國男中音費雪狄斯考(在〈春夜聽冬之旅>)……他借用葉慈的詩題(〈在學童對面〉與〈為吾女祈禱〉),並且從米羅,畢費,德布西,梅湘,凱吉等人的作品得到啟發(〈吠月之犬〉,〈小丑畢費的戀歌〉,〈雪上足印〉,〈給梅湘的明信片〉,〈公開的籠子〉)。寫詩對他已成為一種與世界交通的方式,每一首詩可以說是一封寫給世界的「親密書」。
在〈島嶼邊緣〉這首詩,陳黎把位於太平洋,在地圖上縮成四千萬分之一的台灣島,比做一粒鬆落在藍色制服上的黃鈕釦,個人的存在則如一縷透明的線。只要心——「另一粒秘密的釦子」,緊貼胸前像「隱形的錄音機」——不墜落,人們即可永遠收聽到世界的聲音。詩人雖然卑微,他手中的筆卻能如針一般「穿過被島上人民的手磨圓磨亮的╱黃鈕釦」,用力刺入「藍色制服後面地球的心臟」。懷抱對生命的深刻理解與對詩的信念,詩人將島嶼邊緣變成詩的中心。
——原載《親密書:英譯陳黎詩選1974-1995》
(1997年書林出版公司)
詩評家,翻譯家,多次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著譯有
《現代詩啟示錄》,《親密書:英譯陳黎詩選》,《女性沈思錄》等。
編有《八十三年短篇小說選》(爾雅)。
【前往】
回首頁 陳 黎文學倉庫 Mail![]() me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