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色照在三線路」,這首一九三三年鄧雨賢編的曲、周添旺寫的詞,源自馬偕醫師來台時採的平埔族人的歌,我從年輕對月唱到此際,由愛情的清愁強說唱到人生行路的漸覺苦澀。在幽黯的午夜山徑中,在時挪瞬移的樹影間,低吟這樣一首傳唱六七十年的台灣歌謠,終不成調。
|
|

.................................
向陽在九歌出版的著作可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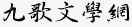
|
|
 .................................
|
向陽工坊
向陽詩房
|

|
|
|
|
|
月色照在
|
向陽

|
|
|
|
|
午夜的山村,月色照在幽隱黯寂的山徑,山徑兩旁的人家都入寐了,月光靜靜柔柔,領著小徑隱入左方更深的山間,右側的溪河攜著薄薄的月暈,清越地唱著歌往山下行去。月色照在三叉路口,月色照落花叢樹影,月色照在夜歸的我走著的這條漆黑細瘦的小路。
哼唱著歌,在我年輕的時候,這小路從山仔后的菁山路蜿蜒而上,舊曆十六的月光下,宛然金箔色的河,由下而上,溯向更高的山崗。午夜的山,沉默不言,把白日的翠綠和風華都丟給黑色的夜去咀嚼,留給柔和的月色去沉吟。走在月光灑過的山徑,唱著歌,即便孤獨寂寞,對影成三,也都有了交代。當時年輕,渴求愛情。渴求而不得,山月就成了寂情的付託。走午夜的山路,唱周添旺填詞的「月夜愁」,在人蹤杳無的山道,在左右為難的路口,我曾經,在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放懷唱出唱給明月相照的歌。
哼唱著歌,在更年輕的故鄉,明月總是由偉岸的鳳凰山山頭升起,斜斜地光暈,斜斜的細雨一般,覆蓋著山村的每一條街道,敲扣那些已經拈掉燈火的柴扉,侵入簡陋的窗口。高中生的我,編織著文學之夢的我,在家人都已入睡的午夜,打開後院的門,凝睇高懸中天的月,一樣唱著母親年輕時也唱的「月夜愁」,在萬般靜寂的夜裡,把心事說給明月聽,把詩寫在月光吻著的稿紙上,安慰自己面對未知人生的年輕的閒情與輕愁。
月色也哼唱著歌,陪我行過服役時南北播飄的山村聚落。桃園虎頭山、中壢龍岡、苗栗三灣一個叫做石馬店的小所在,嘉義大林、台北樹林,還有高雄小港的小山丘,我當兵時跑過的這些所在,午夜站崗的荒郊、墳場、野地,還有膩在二等兵肩章旁失去準星的槍,槍口上插著的無名野花,半夜的野狗嗥啼、墳塋之間遊蕩跋倒的燐光,以及思鄉的苦,都沾染著月的不忍。在面對即將展開的人生行路之前,月色照在三叉路口,伴我走那鬱卒的軍旅春秋。
這些月色,多半落在山村,多半落在我行過的人生的不同坎站。久而久之,月色於我,便飽含苦與澀。即便是在高樓大廈之間偶而探出頭來的月,也警示正通過小巷的我夜行的孤寂。月色照在都市的三線路口,月色照在霓虹閃爍的大道通衢,月色照在人生的某個挫折、某個暗晦之處,像歌詞中「怨嘆月暝」、「無聊月暝」的心緒,難免會被月色漂得更黑更落寞,這世間的肩負、人際的塵緣,名利、地位、聲望與一切渴求,崎嶇險惡,多波多折。進入中年之後,我每每在月升的暗時,感到人生行路的踟躕,遠非年輕對月的輕愁所堪咀嚼。
在皎潔的月色漂洗下,這山間的午夜越洗越黑。「月色照在三線路」,這首一九三三年鄧雨賢編的曲、周添旺寫的詞,源自馬偕醫師來台時採的平埔族人的歌,我從年輕對月唱到此際,由愛情的清愁強說唱到人生行路的漸覺苦澀。在幽黯的午夜山徑中,在時挪瞬移的樹影間,低吟這樣一首傳唱六七十年的台灣歌謠,終不成調。這歌,寫的豈只是少年中輟的戀情?這歌,還寫盡中年望月的心境。人間愛憎,直如月下樹影;而天心月明,或圓或缺,都恍若無聲之雷,轟隆響徹嚜然無語的夜。
──1999.04.30.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3年9月,《暗中流動的符碼》再版改封面,易書名為《為自己點盞小燈》。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