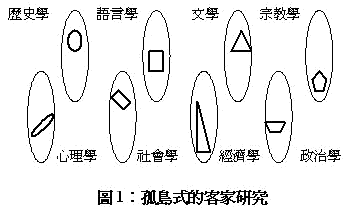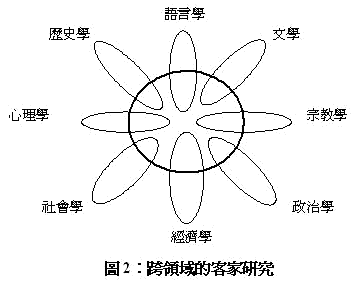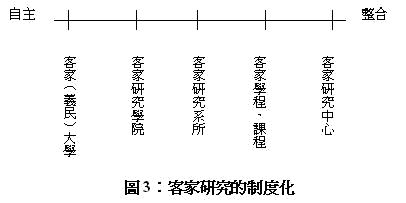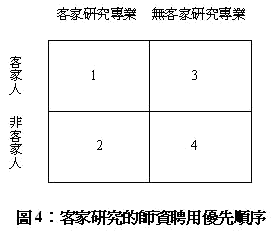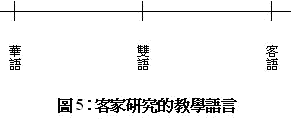|
�@ �Ȯa��s�����* |
||
|
�@ �I���W** �H���j�Ǥ��@��F�Ǩt�[���@�F����s�ұб� |
||
|
�K�n
�b�o�g�פ���Y�A�ڭ̭����N�Q�Ȯa��s�����n�ʡA�]�N�O���A�Ȯa��s�쩳�n��t�ƻ�A���ۡA�ڭ̱N�q�dzN���B�Ш|���c�B�H�Ϊ��|�A�ȤT�Ө��סA���O���Q�Ȯa��s���w��A�̫�A���̱N�˵����e�Ȯa��s�ҭ��諸�x�ҡA�ù��ի�ij���ӥi�檺��V�C Reflections on Hakka StudiesCheng-Feng
Shih,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AbstractWe
will firstly look into the rationales why the field of Hakka Studies has been
justified. In the bulk of this paper, we will seek to delineate what
are required fir Hakka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service for the Hakka. Finally, we will then
scrutinize what barriers it has encountered so far, and seek to provide for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Black Studies is not an end itself but a means to a larger,
more important end. Boniface
I. Obichere�]Ford, 1973: 11�^ When an Indian
breathes, it��s politics. Cindy
Gilday�]Benton-Banai, 2000:
23�^ To remain impartial
in the educational arena is to allow the current partiality to whiteness to
fester. Nathan
Hare�]1971: 3�^ If it is true as
Professor Vine Delorai, that consummate Sioux Indian scholar has said in his
latest essay,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an Indian student can ask
him/her self, is what I am learning useful to Indians?�� (and I believe
it to be), it is even more true that Indian intellectuals must ask, ��is
what I am teaching and writing and researching of valu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dian Nations of America?�� Elizabeth Cook-Lynn�]1991:
13�^ ���B�e�� �u�Ȯa��s�v�]Hakka Studies�^�i�H���O�x�W�Ȯa�B�ʥ�1980�~�N�o�b�H�ӡA�b1990�~�N�l�ͦӨӪ��@���Ǭ�A�i�Ӧb2000�~�N�}�l�i�J��פƪ����q�A�]�N�O�����j�ǫȮa�ǰ|�]2003�^�B��q�j�ǫȮa��ƾǰ|�]2004�^�B�H���p�X�j�ǫȮa�ǰ|�]2004�^�������P�ۥ��C�M�ӡA�ֽ��s���O�_�����n�]�߫Ȯa�ǰ|�B�H�ά����Ȯa��s���t�ҡA���M�|�����즳���}���j�P�Ϲ��n���A�M�ӡA�dzN�ɤ@�����������_������A�Ʀܩ�A�Ȯa�^�]���������٦P���ʪ̪��W�ߩt�ڡC���ަp���A�w�g��J�o����s���Ǫ̡A���U���ϩR�O�p�����@�Ӹ�V�Ǭ쪺�u�Ȯa��s�v�A���鴣�@���@���o�i���ƪ��u�Ȯa���v�]Hakkalogy�^�C �p�G�ڭ̱q���H����|��Ǫ��u�ڸs��s�v�]Ethnic Studies�^�o�ӻ��ӬݡA���ެO�u�¤H��s�v�]Black Studies�^�B�u�ԤB�Ǭ�s�v�]Latino Studies�^�B�άO�u�������s�v�]Native Studies�^�A��_���j�P�O�b1960�~�N��������|�̰ʡA�b���|�B�ʭ��_���餧�ڡA���F�^�����|�j����������ݡA�j�ǯɯɳ]��������t�A�@�譱�q�Ƭ����dzN��s�A�@�譱�i��Ш|�һX�A�]���A�����L�u���dzN�ӾdzN�v���u�¡v�Ǭ�Ө��A�N��s�B�оǡB�H�ΪA�ȳo�T���j�DZЮv���ѳd�Ө��A�o�ǾǪ̩Ӿ�ۤ�L�H�����|�A�ȳd���A�Ʀܩɭn�Q�X�����M�~���P����áA�s����������s�O�_���u�dzN�v�B�H�Φۤv�O�_�u���F�v�A�ȡv�C�b�ۦP���ߵ��U�A�p��T�ߡu�Ȯa��s�v���ۧکw��A�۵M�O�褣�e�w�����D�C ���M�u�Ȯa��s�v���̰��ȬO���Ȯa�ڸs�F�Ѧۤv�A�M�ӡA�u�Ȯa��s�v�ëD���M�`��Ȯa�����A�]�N�O���A�ڭ̩ڵ��Ĩ��M�_�ƥL�B�άO�����ۦu���~�|�A�ӬO�����j���e�Ǧʤt����h�A���O�غc�Ȯa�H�P��L�ڸs�M�Ӧ@�s�����Y�F�]���A���Ȯa�D�骺���h�A���O�إߦb��R���������A�Ʀܩ�n���N�Ѧa�M�D�P��a�X�z���w��A���Ȯa�H�����o�Ӧh���ڸs��a�������i�ίʪ��c���n���C�]���A�u�Ȯa��s�v���ĤG�ӥ��ȡA�O�Q��k����L�ڸs�B�H�ΰ�a�F�ѫȮa�ڸs�C�p�G�i�@�B�Ѥ�Ƹ겣�����רӬݡA�W�@�L�G���u�Ȯa��s�v�A�N�i�^�m�H���̬öQ�����Ѳֿn�C �b�o�˪��{�ѤU�A�u�Ȯa��s�v���u�O���߬�dz��y���@���dzN���A�]�O�@�Ӵ��ѽ��v�]empowerment�^�������@�ӱШ|���c�A��O�@�ǧe�{�Ȯa�ڸs�{�P������ҵ{�B�ڸs��ܪ��¡B�H�γW����a�F�����ۥD����C�b�U���A�ڭ̱N���O�q�dzN���B�Ш|���c�B�H�Ϊ��|�A�ȤT�ӭ��V�A�����u�Ȯa��s�v�����[�C �L�B�dzN��� ���b�H�Ȯa����s�D�骺�߳��ӬݡA�Y�n�ɩw�u�Ȯa��s�v����H�]object�^�A�ե��n�]�t���v�]�O�СB�g��^�B��ơ]�y���B�v�СB��ǡB���N�B�߫U���ͬ��覡�^�B��ס]�F�v�B�g�١B���|�^�B�{�P�B�߲z�]�L�Y�B���ȡB�@���[�B���ǡ^�B�H�ΰ^�m�A�]�N�O�e�ǥ���㦳�Ȯa�g�窺�D�D�A�p���@�ӡA�~���i�৹��a�]holistic�^�e�{�Ȯa�ڸs�������C ���L�A���p��L���쪺�Ǭ�AĴ�p���u�M����s�v�]Peace Studies�^�B�u���k��s�v�]Woman Studies�^�B�άO�U�ءu�ϰ��s�v�]Area Studies�^�A�u�Ȯa��s�v���i��Q����DzΪ��H��B�άO���|�Ǭ�Ҳ[�\�A���ɡA�u�Ȯa��s�v�p���֦��DzξǬ쪺�S���M���B�o�S�P�ɯ�����������ۥD�ʡH�Ĥ@�ؤ覡�O�N�W�z�D�D�����b�U�ӻ����Y�]��1�^�AĴ�p���v�ǡB�y���ǡB��ǡB�v�оǡB�F�v�ǡB�g�پǡB���|�ǡB�άO�߲z�ǡA�A���ձN�U�ӻ�쪺�Ȯa��s���O�[�`�_�ӡC
���D�O�A�U���쥻���ۤv����s���ߡA�Y�ϯ�A�Ǫ��@�N�N�Ȯa�C����s��H�A�o�n���糧��b�z�סB�H�Τ�k�W���]���A�λ������O�_���ѥ|���ҷǡA���ɡA�Y�Ϧb�U��줹�\�U�ҧ������Ȯa��s�A���ȱN���p�L�v�����t�q�A���h�u����h�����]multidisciplinary�^���Ǫ̦@�����|�A��X���u�@�۷��}�d�A�N���p�ݯʪ����ϹC���A���Ѫ��ֿn�۷��x���C �۹�a�A�p�G�n�@�u���������]interdisciplinary�^��s�A������u�Ȯa��s�v�������@�@�ӡu�M�~���v�]discipline�^�A�Ө�L�����u���O�Ȯa��s�̪��@�����h���u�M���v�]subject area of
specialty�^�]��2�^�F���ɡA�b�E�J������s���V�U�A�~���i�ಣ�;�X�ʪ���s�涰�CĴ�p���A�@�W�M���O�벼�欰���F�v�Ǫ̡A�o���L�γ\�|���K�ҹ�Ȯa�ڸs���벼�欰�A���L�A�X�o�I�h�b�O�b�i���e���R���ڡA�ӫȮa�u�O�˵����ڸs���V���@���W�ةʼƭȡA�λ��A�٦���L�P�˭��n�����V�����[��B�άO����F�۹�a�A�@�ӥH�Ȯa�F�v�欰�C����s���ߪ��Ǫ̡A���F��������ƬF�v�Ǫ���¦�V�m�A���w�|�N�Ȯa�[�I���@���J���D�b�A�Ө�L�ڸs�B�Ϊ̬O���������F�v�Ҧ��A�u��Ψӷ��@��ӲաA���y�ܻ��A�Ȯa�]�����ӬO�Q���@�W���ܼơ]independent variable�^�A���藍��û��Q�����i���B�i�L�������ܼơ]intervening variable�^�Ӥw�C
�H�ثe�ͤ��ݵo����ϭ����ӻ��A�g�L�ĤC���˪k�ץ�����ס]2005�^�A�]�N�O�ҿת��u��|��b�v�A�Y�N�b2007�~�|�檺�ĤC���ߪk�e�����|�A���F��|�u����225�@�113�u�A�ϰ���|�N�����אּ��@��ϡ]�۹�h�ƨM�^�A�b�o�˪����|��פU�A�Ȯa�^�@�A�~�ߥ��ӫȮa�ڸs�ѻP����ʨưȪ��Ŷ��|�Q�j�T���Y�C�M�ӡA���������|�ҩe�U�i���ϳW�����Ǫ̨ӻ��A��a���ӬO�j���L�p���A�Ө�ת��]�p�]���ӬO�⪼���A�]���A�S�����n�S�O�Ҽ{�Ȯa�ڸs���ݨD�F�M�ӡA�F�v���ǡ��F�v�z�|�i�D�ڭּ̤Ʊڸs�N���ʡ]minority�^����a�����ʪ��N�q�A�P�ɡA�]���w���ڸs�Ĭ�]conflict prevention�^���n���@�ΡA�]���A�D�Ȯa��s�Ǫ̪����Ӥ����A���F���i��O�H�@��ƨӱ����ۤv���F��D�q�H�~�A�]���i��O�������Ȯa���Ѥ����A�S�����쪺����D�q�A���@�N�����U�ݡB�άO�Ĩ����쪺�X�@�A���M�N�K���F���K�y��ƪ����|�A��s���G���|���q��ڸs���Y���M�ӵo�i�C �۹�a�A�D�H���p�D�v�A�Ȯa��s�Ǫ̷��M���|�����Ӧ��o�˪��D�[�ʰj�סA���L�A���ɡA�̤j���D�ԬO�����������M�����Ү�滛�AĴ�p����F�v�ǡB�άO���|��סF�Y�Ϧo���L�����ܼ��S�w���D�D�A���L�A�u�n��ƥR�����F�v�ǰ�¦�V�m�A�]�A��ǭ��ǡB��s��k�B�H�ΰz�סA�n�z�L�{�������m�n��J�ǡA�ëD�����i�ΡC���M�A�b�u�Ȯa��s�v��Ъ�����A���K�n�V�ݩ�Dzλ�쪺�F�v�ǬɨӭɱN�A�߱��������]guru�^���Ǫ̧�J�A�q�Ƴ��w��¦�B�H�ζ}�ݻ�쪺�u�@�F�b�l�D���d�T���L��ɴ��A�H�ץͩ^�m�dzN���ӷ~���Ȯa��s�͡A�ե��n�ܤ֨��o�Dzλ�쪺�ƭס]minor�^�A�~����O�b�ۥߪ��ᤧ��A����Dzλ��P�u�Ȯa��s�v���s���y�����ȡC ���L�A��ڥ������D�O�A�s���u�Ȯa��s�v�i�H���@�@���M�����ܡH��i�@�B���A�쩳�u�Ȯa��s�v�n�p��~�ন���@�ӾǬ�H�ҿת��u�dzN���v�]academic discipline�^�A�i�H���T�ةw�q�G�����A���i�H���O�@�����N�]art�^�B�άO�����]craft�^�A���t�ۥ������v�����F�A�ӡA�o�i�H�N���@�اӷ~�]vocation�^�B�άO�I��]calling�^�A���F���D�������ʽ�A�٦��R�����^�m�N��F�̫�A���N���ۤ@�رM�~�]profession�^�A�i�H���O����Ǫ��Ѫ��H���]Goodin &
Klingemann, 1996: 4-5�^�C�p�G�H�M�~�����רӬݡA�C�ӾdzN����������ۤv���P���M�~�n�D�A���F�_�X���M�~�۲z�B���|�d���B�H�ά�s��O�H�~�]Goodin &
Klingemann, 1996: 6�^�A�٭n�]�A�������@�P���߳��B���䷧���B�֤߽��D�B�D�n�z�סB��s��k�B�H�έ��j�D�ԡ]Karenga, 1993: xv;
Anderson, 1990: 2�^�C �ѩ�Ȯa�ǰ|�O�b�u�Ȯa��s�v�������e�N�w�g�]�ߡA�]���A��쪺�o�i���o�b�N���e�i�����A���_�a�i��ۧکw�q�B�H�νվ�A�S�O�O�����B���D�B�z�סB�H�Τ�k�C�p�G�ڭ̼ȥB�N�u�Ȯa��s�v�w�q���u���t�Φa��s��ئ]���A�b��ر��U�A�|�p��v�T�Ȯa�ڸs�v�A����A�ڭ̦ܤ֥����b�߳�����B���@�ѡC �N�߳��Ө��A�ڭ̥H���A�u�Ȯa��s�v���ӬO�u�H�Ȯa�����ߡv�]Hakka-centered�B�άOHakkacentric�^���Ǭ�A�]�N�O�j�եH�Ȯa���[�I�A�ӧe�{�Ȯa�ζH�B�H�θ����Ȯa�g��F�P�ɡA�ڭ̧Ʊ�H��P���A�סA���F�n�ȥ����v�ݾl���t���誩�L�H�A�٭n�b�F�Ѧۧڪ��L�{���A���յۥh��������Ȯa�H���{�P�F�̫�A�ڭ̧Ʊ������B���V�X�Ȯa�ڸs�ҥ��ߪ��N�ѧκA�]�άO�z���^�A�H�O�٫Ȯa�ڸs���s���v�Q�]group rights�^�B�H�α��ʫȮa�H������֬�C �o�˪��~�|���[�c�A�I����O���t�۴X�������۩������]�C�����A���b�T�߫Ȯa�ڸs�s�b���j�e���U�A�Ȯa�g�禳��dzN��s�W�����ȡF���ۡA�Ȯa�g��i�H�ϥά�Ǫ��覡�Ӭ�s�A�]�A���T���y�z�B�X�z�������B�H�Φ��Ī��B��F�̫�A���O�q�ڸs���Y�B�٬O��a���骺�߳��ӬݡA�ڭ̬۫H�Ȯa�g�禳�䥿�����^�m�A�ר�O�b�����F�����W���W�C ���A�N�F�v���Ǫ��h���Ӭݡu�H�Ȯa�����ߡv�A�ڭ̭����n�G�_�ڵ����Ȯa�ڸs�ҥ[�������B�[���B�άO�t�O�ݹJ�A���ެO���v�����B�٬O�s�@���F�ڭ̤]���M�Ϲ����Φ����P�ƬF���B�άO�ĦX���I�A���ެO�j�O�G���B�٬O�`�`�����A�]���ެO�Q�������B�٬O�D�ʿ�ܡF�ڭ̧�n�j�P�D�i��a���ּƱڸs�v�Q���O�١A���ެO�F�v�B�g�١B���|�B�٬O��Ƽh���C �ѡB�Ш|���c �u�Ȯa��s�v�@���Ш|���c�A�i�H�q��F��´�B�v��u���B�оǥλy�B�H�νҵ{�w�Ƶ��X�Ӽh���Ӧҹ�C�����A�N�u�Ȯa��s�v�w���ߩR����F��´�Ө��A�N��פơ]institutionalization�^�����ФW�Ӭݡ]Champagne & Stauss, 2002:
3-6�^�A�i�H�ѦۥD�ʳ̰����Ȯa�j�M�|���A���i���X�j�Ǹ��Y���Ȯa�ǰ|�A�άO���X������@�t�ҡB�ǵ{�B�άO��s���ߡA���@�Ө��]��3�^�C�N�Ȯa�j�ǦӨ��A�ѩ�v�ͳ��O�ѫȮa�H�Һc���B�άO�H�Ȯa�H���D��A�dzN�W���M�|�H�u�Ȯa��s�v�����ߡA�z�פW�ݨӡA�դ��������դ�ջڪ������X�e���F���A�v��B�H�νҵ{���w�Ƭ۹�W�|����X�z�A���|���]�H�}�ҡB�άO�ѻݤ��Ū��������p�C���L�A�p�G�v���Y�歭��b�Ȯa�����A���ȷ|���ڸs�j�����ĪG�A�]���A�u�n���l�`�Ȯa�D��ʪ���h�U�A�����A�}��W�B�A�i�H�N�D�Ȯa�v�͵����ڸs������IJ�������C
�ĤG�ئw�ƬO�Y�p�d��A�b�{�����j�Dzz�Y�t�~���߫Ȯa�ǰ|�C�ѩ�O�|�Ū��s��A�t�Ҥ����ۦ��@��A�v��B�ҵ{�W�i�H���q���L�F���~�A�u�n�������Dzλ�줣�n�ۮt�Ӥj�A�]����X��s���Ŷ��C�̭��n���O�A�ѩ��㦳�۷��{�ת��W�ҡA�|���n�b�հȷ|ij�W�����g�O�ɧU�B�H�ƭ��B�B�άO�w��Ŷ��A�٬O�i�H�C�b���l�C���L�A�p�G�ǰ|�O�ѭ쥻���t�ҡB��s���ߡB�άO�@�P��ء��q�ѱШ|�����X�s�ӨӡA�i��|������{�����v��ӥX�{�]�H�]�ƪ����p�A�i�ӳy���L�k�u����M�~�H�諸�~�ҡC���Y�������p�A�O�j�Ǧp�G���w�n�ߡA�u�O���̬������i��Ѻ�`���w��س]�A�{���]�F�M�|�B�]���F�q�A�p���@�ӡA�Ȯa�ǰ|�N�u���L�O�u�����L���]���F�@���~�Ӱ]���_���A�Ȯa�ǰ|�_���դ����t���^�l�A�Ʀܩ�i��Q�����૬�����|��ǰ|�C �ĤT�ر��p�O�]�߫Ȯa��s���ߡB�Ȯa��s�ǵ{�B�άO�Ȯa��s�t�ҡA�i�H���O�@��j�ǹ��h����ƥD�q���_�X�^���A�i�H���Ȯa�B�H�ΫD�Ȯa�ǥ;DZo�Ȯa�g��C�@��Ө��A�Ȯa��s���ߥi�H��O�w�]�Ȯa��s�t�Ҫ��v�y���D�A�q�`�u��²�檺��s�H���A�S����O�}�]�ҵ{�C����A�Ǯեi�H���b�Dzλ��A�ն}�X���a���Ȯa�������ҵ{�AĴ�p���v�ǡB�y���ǡB�H���ǡB�άO���|�ǡA�榳�l�O�A�γ\�i�H���ո�t���Ȯa��s�ǵ{�A�S�O�O�b���ǥͻݨD�����p�U�F�o�˪��ǵ{�A�i�H�Ȯɩ}�N�b��@�t�Ҥ��U�A�]�i�H�b�ǰ|���U�B�@�F���v��B�H�ξǥͳ����۷��ӷ�����A�W�ߪ��t�ҴN����릨�B�I�����X�C���L�A�Y�ϫȮa�t�Ҥ��A�H�H�X�U�A��_�Ȯa�ǰ|�A�b���ѤW�٬O���դ��v�����H���A���D�O���Ӧۮե~���T�w�����A�~�|�Q�������ج۬ݪ��������C ������u�Ȯa��s�v�Юv�B�άO��s�H�����u�ΡA�s���n��Ʀ�ذ_�X������H�ڭ̥i�H�q�Ȯa�����B�H�αM�~��O��ӭ��V�ӫ�ҡ]��4�^�C�����A�ѩ�C�ӱڸs�����ۤv�W�S�����v�g��A�o�O�L�H�L�k���N���A�]���A�b�z�Q�����p�U�A���ӬO�ѫȮa�Ǫ̨Ӿ���C�ĤG�ӭ��V�O�q�ƫȮa��s���M�~��O�A�i�H�[����Х]�A�O�_�b�Dzλ�챵���Y�檺�dzN�V�m�B�ӳդh�פ�O�_�P�Ȯa��s�����B�Ϊ̬O�_���L��������s�C�N�z�פW�ӬݡA�dzN�V�m���ӬO�_�X���n�D�A�_�h�A�O�S����k�t��W�߬�s���d���F���D�O�A����O�����N�����N�@�i��Ȯa��s�A�]�N�O���A�p�G�u�O�@�Ӿ��|�D�q�̡A�o���L���L��O�����o��¾�B�A�������P��b�Dzλ�����o�Ǧ쪺�t�ҡA���M����H����u�Ȯa��s�v���O�P�u�A�]���A�s���ӽЪ̪��Ǧ�פ�B�άO��s�p�e�O�_�����A�ܤ֥i�H��窥�O�_����s�ʾ��Ȯa�C
�ھڤW�����Q�סA�̨Ϊ��Ȯa��s�����ӬO�P�ɨ�ƫȮa�����B�S�O�㦳�Ȯa��s�M�~��O�̡F�۹�a�A�̤��A�����H��O�J�D�Ȯa�H�B�P�ɤS�ʥF��s��O�̡C���D�O�A�b�Ĩ��ץh�k�i��z�蠟��A�ڭ̭��諸�D�ԴN�O�u����vs.�M�~�v����ܡA�]�N�O�A�쩳���M�~��O���D�Ȯa��s�̡B�٬O�S���M�~�g�窺�Ȯa�H�A��̥i�H�C���u���Ҽ{�H��h�W�A�ڭ̻{���M�~��O���g�����ӬO��Ȯa�������n�A�]���A���D�O�@���n�ժ����U���~�̡B�άO�����H�h�A�_�h�A�b�@�ӷs�Ъ��dzN���A�n�P�ɰV�m�@�ӷs�H�B�o�S���ݦo���L�q�ƱоǬ�s�A�X�G�O��n�������F�]���A���D���b�j�dz����I�����о����O�A���ӧ�o�˪��ůʼȮɫO�d�A���h�u���@�ӭݥ������v�C �M�h�A�u�Τ@�W�㦳�M�~��O���D�Ȯa��s�̡A�ëD�����S�����I�C�����A�ڭ̾�ߪ��٬O�u�ഫ�̡v�]convert�^�A�]�N�O���A�b�H�B��ƪ����p�U�A���n�u�Ȯa��s�v������ǡA�ե����H�b�Dzλ���ܫȮaij�D�@���Ǧ�פ媺�D���A�]���H�γ\�u�O���F�ӽЬ�s�p�e�h�@���D�ӵy�@�վ�A���ެO���o�Ǧ줧�e�B�άO����i�浦������V�A�ڭ̵L�k�O�Ҧo���L�O�_�@�N��@�������ߤO�O�d���u�Ȯa��s�v�C�ڭ̥H���A���F���z�L�u�����e�����ͨӮǺV�����H�~�A�ߤ@�వ���N�O�u���᪺�w����Ų�AĴ�p���A�������w���۷���v����s�����Φb�u�Ȯa��s�v�F���A�Y�ϬO�@�Ө㦳�M�~��O���Ȯa��s�̡A�ڭ̤]�������ݦo���L�J��H��A�|�p��M�w���s��O���t�����Dzλ��B�H�Ρu�Ȯa��s�v�C ���A���ެO�_�㦳�Ȯa�����A�̧x�����٬O�p�����Ȯa��s�̨㦳�Ȯa���u�ӷP�סv�]sensitivity�^�A�]�N�O���A�p�����|��Ȯa�ڸs�b�E�p�x�W���L�{���A�b�ʥF�{�N��a�O�٪����p�U�A�p�����e���D���w���ߩR�C�@�Ӹg�L�M�~�V�m���Ȯa��s�̡A�]�\��Ƭ��������ѡB�q�ƹL��������s�B�]���j�P���J���ʾ��A�M�ӡA�u�n�o���L�L�k���o�Ȯa���P�z�ߡ]empathy�^�A����A���X�Ӫ���s���G�B�άO�F����ij�A�Y�D�B�����v�A�����i�ण�ūȮa�ڸs���ݭn�A�Ʀܩ�P�Ȯa�ڸs���Q�q���D�ӹ��C�ڭ̥H���A�p���[��u���e�ѻP�M�~�u�Ȯa��s�v���骺�g���B�H�ΧV�O�i��u���᪺�P�����|�ơA�γ\���ҧU�q�C �̫�A�쩳�Ȯa��s�Ǫ̬O�_�@�w�n���o�Ȯa�ܡH�H�dzN��s���зǨӬݡA�p�G�@�ӱq�ưϰ��s���H�S�����a�y����O�A�ե��b�Ĥ@����m�����o�W�����ê�A�Y�ϬO�����ƪ�½Ķ�]�I���U�A���K����k�ҡF�ר�O�b�i��Ĥ@�u����s���ڡA�ե��n�����Ķ�H���B�άO��ƴ��Ѫ̡A���K���j�u�k�o���ʾѡC�]���A�Y�Ϥ���ƫȮa�����A�_�X���Ȼy��O�O���n���A���D�O�o���L�Ҷi�檺��s���αq�ƥг��լd�B�άO�P�Ȯa�H��������ܡC �ܩ�оǤ譱�A�N������j���Q�תŶ��A�S�O�O�j�dz����ҵ{�A�N���ЦӨ��A�i�H�ѳ̷��ݪ��W�L�ػy���_�ʸܡA���i��ػy�P�Ȼy�åΡA���Q������ĥΫȻy�]��5�^�C���M�ڭ̨èS���k�w����a�y���B�άO�x��y�A���L�A�ԫ�H�ӡA�ػy�o�O��誺�u��y�v�A�Ш|���Ʀܩ@�ӱ`�]���u��y����e���|�v�A�]�]���A�ػy�Q���@�оǻy���A�ܤֳQ��áF�Y�Ϫ�~�Ӧb����p�Ǧ��ҿת��u�m�g�y���v�оǡA�M�ӡA�C�g�u���@�`�ҵ����G�ơA�M�����~�B��ƵL�ɡC �M�ӡA�q��ڤH�v����y�Ӭݡ]�I���W�A2004�^�A���y���ЬO���H�v�A�S�O�O���ּƱڸs�Ө��A�y���N�O��ô�ڸs�R�ߤ��i�ʤ֪��n���C�S�O�O���Ȯa�ڸs�Ө��A�y���O�w�q�Ȯa�{�P�̬��K�������[����A�]���A���[�H�ӡA�u�٧ڥ��y�v�@���O�Ȯa�B�ʳ̭��n���D�D�F���A���ѫȻy���ҥH�|��s�A�i�H�j�P�k�S�Ϊv�̦b�ʦ~�өұĨ����u��y�F���v�C�b�o�˪��j���Ҥ��U�A�H�Ȯa�ܨӶi��D�y���Ȯa��s�ҵ{���оǡA���M����ٱo�W���O�½ëȮa�{�P���̫���S�A���L�A�ܤ֥i�H��Ӫ��Ȯa�^�A��y�t�@�ӫD�ͬ��Ȯa�ܪ��Ŷ��A�]�N�O���A�Ȼy�]�i�H�@���Ш|����ǥγ~���y���F���D�Ȯa�ǥͨӻ��A�ר�O�Ӧ۫D�Ȯa��m�a�Ϫ̡A���F���P�żƪ��Ȯa�y���ҵ{�H�~�A�o�Ǥ]�i�H���@�Dz߫Ȯa�ܪ��i���B�νҵ{�C ���L�A�Y�Ҽ{��ëD�Ҧ����v�ͳ����ګȮa�ܡA�ܤ֦b�{���q�A�i�H�ĥΫȡ������y���覡�оǡC�j��Ө��A���y�]bilingualism�^���T�ؤ覡�A�Ĥ@�جO�ĥΧ{���ҿת��u�۵M�y�v�覡�A�]�N�O�b�Ұ�W�H�ػy���оǥD��A�A�A�צa�ﴡ�Ȯa���J�A�ר�O���D�Ȯa�ǥͦӨ��A�γ\�i�H���`�Ǻ��i���νw�B�աA������|���ͻq�����e���Pı�F���L�A�o�زV�f�����y�о����K�|���ǥͦ��u���������v�]diglossia�^���{���A�]�N�O���A�~�H���ػy�~�O�D�n���y���A�ӫȻy�u��@�����n�j�������U�ʻy���A�]���A�o�����y�ҵ{���ӥu�O�J���ҵ{�B�άO�L��ʪ����k�C �ĤG�����y�оǬO�H��t�@���������d��A�]�N�O���A���F�Y�ǽҵ{�H�ػy�оǥH�~�A�S�O�O�s�ͪ������A��L���~�Ū��ҵ{�����ĥΫȮa�оǡC�o�˪��w�Ƥ覡�A�̤j���u�I�N�O���y�ǥ;��֦b�~��������o�Ȼy��O���˩w�A�p���@�ӡA���ǥͲ��~���ڡA�N�i�H�P�ɨ�Ƭ۷����Ȼy��O�C���L�A���D�Юv�]���������y���˩w�n�D�A�_�h�A���ګȻy���Юv�N�û��u����Ъ�Žҵ{�C���M�A�o�˪����y�оǥ����إߦb�@�Ӱ��]�A�]�N�O�y����O�������W���ݨD�A�_�h�A���ȥu�����Ӷi�@�B�q�Ƭ�s�̡B�άO���۷��ϩR�P�̡A�_�h�A���ȩۥͤ����C �ĤT�جO�Ĩ��������y�оǪ��覡�A�]�N�O���A�o�O����ʪ���ҡA�P�@�ؽҵ{�P�ɶ}�]�Ȼy�B�H�εػy���Z�šA���ǥͦ���ת��ۥѡC�����A�o�����b�v�꦳�۷��W�Ҫ����p�U�A�~���i��p�����צa�}�ҡA�]���A���D�O�@�ұM�����Ȯa�j�ǡB�άO��¦�ҵ{�A�@��Ȯa�ǰ|���ȬO�ߦ��l�ӤO�����C���~�A�Y�ϥ���ҵ{�}�o�X�ӡA���D���S�O�����]�B�άO��ҤH�ƪ�����A�_�h�A�p��ǥ����Ȼy�оǽҵ{�A�N�O�ҵ{�W�����@�j�D�ԡC �����ӬݡA�Ȯa�j�����ӬO�n���l�D���ؼСA�_�h�A�b�ثe�H�z�u��Ǫ����覡�ӦҮ֤H����|��Ǫ��x�ҤU�A�Ǫ̩������F�ɵ��ӳQ���i��������o�q�Ƶ�Ų����s�A���o���N�פ�g�@��V�վ㬰���Z�W�C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B��Ǥޤ�����^�B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B���|��Ǥޤ�����^�BEI�]Engineer Information�B�u�{���ޡ^�BA&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B���N�P�H��ޥί����^�B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B�O�W���|��Ǥޤ�����^���dzN���Z�A�Ȯa�ǰ|���t�Ҫ���s�ե��n�����o�Ǿ��c���즨�ߪ��v���C�Y�ϨS���o�˪����O�A�Ȯa��s�Ǫ̤]�n���ɾD��Dzλ�쪺��áB�άO���b�A�Ʊ�N�ۤv����s�ɦV�u�D�y�v�A�]���A�ߦ��b�W�ߦۥD���Ȯa�j�ǡB�άO�Ȯa�ǰ|���|�����j�ժ��@�����U�A�_�h�A�Ȯa��s�Ǫ̪��ɵ��L�{�@�w�|����T��C �v�B���|�A�� �Ȯa��s�̥����M���a�ۧڦa��A�ѩ�u�Ȯa��s�v�����O�Ȯa�B�ʪ��A�͡A�]���A���F����s�B�оǵ��dzN�d���H�~�A�٦��@�����Ѥ��l�����|�A�ȸq�ȡA�_�h�A�N�u���L�O�Q�ҿץD�y���|�Үج[���j�ǧl�Ǫ��˪O�}�F�C�N�u�Ȯa��s�v���ؼЦӨ��A�ڭ̥i�H�ѫȮa�ڸs�B�ڸs���Y�B�H�ΰ�a�T�ӭ��V�Ӧҹ���ȡA�]�N�O�Ȯa�ڸs�ۧڻ{�P���غc�B�P��L�ڸs�i��ﵥ�����ʡB�H�λP��a���X�z�w��C���F���@�����i�Ȯa�^���n�x�B�H�ξ���Ȯa�ڸs����ޥH�~�A�u�Ȯa��s�v�]�i�H�@���ڸs������ܪ��¡A���~�A�٥i�H�ۥD�a�ɩw��a������C �����A���Ȯa�ڸs�����Ө��A�u�Ȯa��s�v���̰n�D�A�N�O�p�����Ȯa�ڸs�F�Ѧۤv�B���s�e�{�ۧڡC�ڭ����ӥi�H�P�N�A�b���������v���Ҥ��U�A�Ȯa�H�b�x�W���o�i���䧢�V���߸����{�A�S�O�O�b����H�Ƹ��h���ԫn�H�B�H�αj���k�]�]ascribed�^�S�����@�ơ]homogenized�^���F�v��ơA�Y�������P���B�A���N�O����䶫�ơB�άO�ۧ����ΤơA�S�O�O�~�|�Ϫ��^�F�Y�Ϥ@�V��@�W�ߪ��Ȯa��m�]��˭]�B����^�A�H�۫��m�t�Z���Ԫ�A�~�Ӫ�������ۦa�R�E�۩T����쪺�w���P�C�`���A�Ȯa�H������{�P���ﭫ�s�Q�������D�AĴ�p���G�s���Ȯa�{�P�O�p�͡B�����B�άO�o�i�H�Ȯa�g�禳��S�O���B�H�@���Ȯa�H���Pı�O�ƻ�H�Ȯa�N�ѬO�p�ͪ��H�Ȯa�����O�p����o���H�Ȯa�L�Y�����جD�ԡH�H�ΫȮa�H�i�H�����˪��վA�H �u�Ȯa��s�v���F���߫Ȯa�ڸs�������ۧکw�q�A�]�n���h�Ȯa�H�P��L�T�ӱڸs����IJ�A�p������Y�ص{�ת��t���ɽu�AĴ�p���G�Ȯa�ڸs�b�������ڸs���c���A�s���v�O���Y�p��H�Ȯa�ڸs�s���n��t�W���䨭�B���۷��͡B�٬O����̪�����H�Ȯa�ڸs�P��L�ڸs�����ʡA�s���O���ɡB�٬O�����H�Ȯa�ڸs�P��L�ڸs�������A�s���O�n�����T�w���Ҧ��B�٬O�n��ij�D�@��ܩʪ����ʽվ�H�o�ص����O�n���w�b�^�B�s���B�٬O�����h���H�s���x�W�Ȯa�H���ڸs�g��A�P���~�x�W�Ȯa�H���P�H�P����B�F�n�ȡB�άO�@�ɨ�L�U�a���Ȯa�H�O�H ���M�A�u�Ȯa��s�v�٭n�z�L�ڸs�F�����W�e�A���ڸs�P��a���������Y���X�ب��A���ɡA�������w�줣�u�O�������Ȯa�ڸs���N���H�B�άO�ڸs�����թM���ĤT�̡A�Ʀܩ�n���ɬ���a�F���D�ɪ̡AĴ�p���G�s����a�O��t�ʱڸs���u��B���[�����P�B�٬O���Ѥ����C���W�h���ۥD����H��a���ڸs���Y�O�n����۵M�B�٬O�n�������J�H�s���o�O�@�ӳ�@��ơB����ơB�Ѥ�ơB�٬O�h����ƪ���a�H�s���o�O�@�ӵؤH���~�H����H�]Chinese�^���D����a�B�n�q���ڡ]Austronesian�^���D����a�B�٬O��̤@�˭��n�������ڰ�a�H�o�O�@�ӭ�����ڡ]indigenous peoples�^��a�B���ޡ]settler�^��a�B�٬O�����]immigrant�^��a�H��a���ӵL���ڸs���t���B�٬O�����[�H�ӻ{�H�ڸs�������t�����ӬO�v�����u�B�٬O��פƤ���n�H��a���Ӱl�D�ڸs�������ĦX�B�٬O�M�ӡ��M���H�p�G�n�i��M�ѡA���L�h�������q���ڸs�����A�O�n�Ĩ���ѡB�H�ơB�٬O���諸�A�סH��a���Ӯ����Ķi��Ϫ[���B�٬O�n���a�O�٤ּƱڸs���v�Q�]minority rights�^�H�s���֤~�O�ּƱڸs�]ethnic minority�^�H�O�_�n�]�w��a�y���B�x��y���B�άO�q�λy���H ��B���y �p�G���u�Ȯa��s�v�O�{�N�Ȯa�B�ʩҶʥ͡A�Ӳ{�����Ȯa�ǰ|�O�F�v�H�����F���A����A�@���u�Ȯa��s�v���s���@���l�A�ڭ̪��d��������ӤH�M�~����i�B�άO�º�dzN��쪺�إߡA�ӬO�٭n���ۨ}���ӱq�ƫ�Q�һX�u�@�B�H�ΰ��i�㦳�Ȯa�믫�����ѥ��l�F�]���A�ڭ̨ä��������Ȯa�{�H����������y�z�A�٭n���եh�����쩳�O���Ǧ]���غc�Ӧ����A�n�h���R�Ȯa�{�P�p��v�T�Ȯa�ڸs������欰�A��n�w��Ȯa�ڸs�B�ڸs���Y�B�H�ΰ�a�w��A���X���Ī��F���ب��C �p�G���H�]���Ȯa��s�̰��۩�p�������|���h�A�i�ӳQ�����o�O�u�F�v���T�v�A���n����o�Ǥ����H���Ϥ��̧@���dzN�^���ƺC�F�p�G�o�ǤH���l�̯u����ߪ��A�O�Ȯa��s�̥��}�{�������ê����c�ʡB�Ʀܩ��ƩʼɤO�A����A�L�̤��ȬO�L�d�����[�̡B�άO���g�N�����q�̡A�ӥB�O�o�ؤ�t���Y���W�N�����B�Ʀܩ�O�c�N���[�`�̡C �ƹ�W�A�ھ�Garza�]1999�^�����꾥����Ǭ�s���ҹ�A�ּƱڸs�Ǫ̡]minority scholars�^����s�A�å��]���ۨ����F�v�H���B�άO���ڸs�����h�Ӧ��Ҵ�l�A�]���A�ҿסu�������[�B�Y�ԡv���C���A�u�|��ê�~����������DZq�ƾ�����Ǭ�s�CLowy�]1995�^�Ʀܩ�D�i�A�쥻�o�DZڸs��s���c���]�ߡA���F�����ѤW�����ȡA�F�v�W������d���C �ھ�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2001�^�A�D�w���j�ǴX�G��������������ڪ��оǬ�s���A�ӭ�����ڡ]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u���F�D�w�`�H�f��2.1%�]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8�^�C�۸����U�A�x�W�Ȯa�ڸs���H�f�ܤ֦��F�`�H�f��12.6%�]����s�A2004�^�A�]���A���O���Ȯa�ڸs�ӻ��A�{�����Ȯa��s�ǰ|���t�ҡ����ߡA��M�����F�p�G�H�ڸs�M�Ӫ��[�I�ӬݡA���D�Ȯa�H�����|�F�ѫȮa�ڸs�A�F�����ӦҼ{�A�W�[�Q���������Ȯa��s���c�C �@ �ѦҤ��m �m���Ȯa�F���n�Cc. 2000�C�L�X���B�G����Ȯa�`���C �i���w�C2004�C�q�Ȯa��s�P�Ȯa�ǡr��Ū��x�W�Ȯa��s�Ƿ|���߮y�ͷ|�u�ڦV�ȾǤ����G�Ȯa�Ǭ�s���^�U�P�i��v�A�x�_�A�x�W�j�Ǫk�ǰ|��ڷ|ij�U�A2��14��C ���B�ɡC1991�C�q�Ȯa�Ǭ�s�ɽסr����}�����s�m�r�ީ�ڸs�M�{�ꤧ���G�Ȯa���|�P��ơn��10-15�C�x�_�G�����ѧ��C ���^���C2004�C�q�ڦV�Ȯa�Ǥ����G�Ȯa�ڸs�v���^�U�P�i��r��Ū��x�W�Ȯa��s�Ƿ|���߮y�ͷ|�u�ڦV�ȾǤ����G�Ȯa�Ǭ�s���^�U�P�i��v�A�x�_�A�x�W�j�Ǫk�ǰ|��ڷ|ij�U�A2��14��C �L���C2004�C�q�Ȯa�Ǭ�s�v���w�w�Ȯa�Ǫ����P�o�i�n�o������F�|�Ȯa�e���|�D��u2004�Ȯa���ѽ¡v�A�x�_�A������N���A12��19��C �I���W�C2004�C�m�x�W�Ȯa�ڸs�F�v�P�F���n�C�x�_�G��Ī�ϮѥX�����q�C �����ʡCn.d.�C�q�Ȯa�Ǫ��w�q����ij�r�]pdf�^�C ����s�C2004�C�m����Ȯa�H�f��¦��ƽլd��s�n�C�x�_�G��F�|�Ȯa�e���|�]http://www.
hakka.gov.tw/ct.asp?xItem=6918&CtNode=518&mp=298&ps=�^�C Anderson,
Talmadge. 1990. ��Black Studies: Overview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Talmadge Anderson, ed. Black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10. Pullman, Wash.: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8. ��2034.0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Australia, 1996.�� (http://www.abs.gov.au/
Ausstats/abs@.nsf/7d12b0f6763c78caca257061001cc588/c159fa62a2e98d2fca2568a9001393e4!OpenDocument) 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 2001. Indigenous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s University
Presidents (http://www.avcc.edu.au/content.asp?
page=/policies_ programs/indigenous/ index.htm). Champagne,
Duane. 1996.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Is for Everyon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0, No. 1, pp. 77-82. Champagne,
Duane, and Jay Stauss. 2002. ��Introduction: Defining Indian
Studies through Stori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Duane Champagne, and Jay
Stauss, eds.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igenous Nations, pp.
1-15.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Press. Cook-Lynn,
Elizabeth. 1991. ��The Radical Conscience i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Wicazo Sa Review, Vol. 7, No. 2, pp. 9-13. Duran,
Livie Isaro, and H. Russell Bernard, eds. 1973. Introduction
of Chicano Studies. New York: Macmillan. Ford,
Nick Aaron. 1973. Black Studies: Threat or Challeng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Goodin,
Robert E.,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1996.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3-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cia,
John A. 1997. ��Latino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and
Power Perspectives for Latino Communit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Discipline.�� JSRI
Occasional Paper, No. 34. Garza,
Hisauro. 1999. ��Objectivity, Scholarship, and Advocacy: The
Chicano/Latino Scholar in America.�� JSRI Occasional Paper, No. 58. Hare,
Nathan. 1771. ��What Should Be the Role of Afro-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in John W. Blassingam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Black Studies, pp. 3-15.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arenga,
Maulana. 1993. Introduction to Black Studies. Los
Angel: University of Sankore Press. Kershaw,
Terry. 1990. ��The Emerging Paradigm in Black Studies,�� in
Anderson Talmadge, ed. Black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7-24. Pullman, Wash.: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ulchyski,
Peter. 2000. ��What Ia Native Studies,�� in Ron F. Laliberte,
Priscilla Settee, James B. Waldram, Rob Innes, Brenda Macdougall, Lesley
MaBain, and F. Laurie Barron, eds. Expressions in Canadian Native Studies,
pp 13-26. Saskatoon, Sask.: University Extension Press. Lowy,
Richard F. 1995. ��Eurocentrism, Ethnic Studie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oward a Critical Paradigm.��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5, No. 6, pp. 712-36. Morrison,
Dane, ed. 1997.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Peter Lang. Poblete,
Juan, ed. 2003. Critical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Stud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ice,
John A. 1978. Native Studies: American and Canadian Indians.
Toronto: McGraw-Hill Pyerson. Robinson,
Armstead L., Craig C. Foster, and Donald H. Ogilvie, eds. 1969. Black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A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Renato. 1985. ��Chicano Studies, 1970-1984.��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4, pp. 405-27. Yang,
Philip Q. 2000. Ethnic Studies: Issues and Approach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o�����j�ǫȮa�ǰ|�|��u�Ĥ@���x�W�Ȯa��s��ڬ�Q�|�w�w���y�����U���Ȯa�P�a����|�v�A�x�_�A��ڷ|ij���ߡA2006/10/29-30�C ** 10699�x�_���l�F�H�c26��447���Fcfshih@mailtku.edu.tw�C �����v�d�j�ǡ]2004�^�B�H�Ϋ̪F�Ш|�j�ǡ]2004�^���O�]���Ȯa��Ƭ�s�ҡC���\�j�ǡ]2003�^�B�}�n�z�ǰ|�]2004�^�B�H�ΥȮN�j�ǡ]2005�^�]���Ȯa��s���ߡC���������c�����M�N�ǰ|�Ȯa���Ϭ�s���ߡ]2003�B��٫Ȯa��s���ߡ^�B�̪F�Ȯa�j�ǫȮa���~��s���ߡ]2004�^�B���^��ޤj�ǫȮa���d��s���ߡ]2005�^�B�H�Ω��s��ޤj�ǫȮa��Ƭ�s���ߡ]2000�^�C�t�~�A���s��Ǥj�ǥx�W�y��Ǩt�]���Ȼy�աB�H�ΰ�߷s�˱Ш|�j�ǥx�W�y���P�y��Ш|��s�ҳ]���x�W�Ȯa�y�աC Ĵ�p�����j�dzq�ѱШ|���߱б¶��������A�u���j�S�����|��ǰ|�A�Ȯa�����v��]���R���A�N�]�߫Ȯa�ǰ|�A�O�F�v�䲼�z�w�Ш|�F���v�]�m�p�X���n2003/11/20�^�C �����u�Ȯa�ǡv���Q�סA���i���w�]2004�^�B���B�ɡ]1991�^�B���^���]2004�^�B�L���]2004�^�B�H�η����ʡ]n.d.�^�C �S�٬��u������Ǭ�s�v�]Chicano Studies�^�F��Duran�PBernard�]1973�^�BGarcia�]1997�^�BPoblete�]2003�^�B�H��Rosaldo�]1985�^�C Ĵ�p�����j�ǫȮa�ǰ|���ߪ��v�����u���i�����dzN��s�P�оǤH�~�B�`�ƫȮa�ǰ�¦�P�Ȯa��s�v�F��http://hakka.ncu.edu.tw/hakka/modules/xt_conteudo/?id=3�C�ӥ�q�j�ǫȮa��ƾǰ|���ؼЦ��G�����n���A���F���ܡu���s�Ȯa�y���Τ�ơA�P�i�����P����o�i���Ȯa��ƥͺA�v�H�~�A�ٴ��\�u�P�i�Ȯa�ڸs�P�ꤺ��L�ڸs�Ʀܥ��y��L�a�ϫȮa���s���}�ʷ��q�pô�A�H�i�@�B�إߦX�@������Y�A���Ȯa��ƫO�s�αڸs�믫�ĦX�@�P�V�O�v�F��http://hakka.nctu.edu.tw/Hakka-A-webpage/hakka_B_002.htm�C |